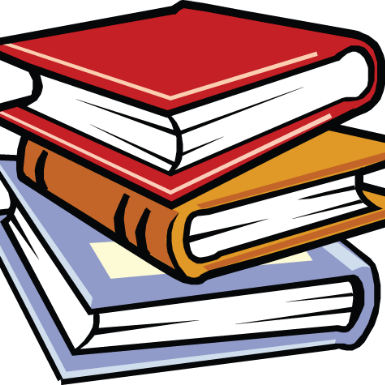天高云淡,大漠孤烟直。
一行鸿雁斜飞。
贺锦心抬眼直至鸿雁消失在天尽头,纵有弯弓射雕之心,却苦于手无寸铁,只能握紧空空的粉拳,恨恨地咬了咬牙。
此刻若能射下一只大雁来,多少给她的父亲带来哪怕最微弱的一点生的希望。
然而她只能舔一舔干裂的嘴唇,将最后一滴水滴在父亲的唇间。
两个官差紧盯着锦心手中的羊皮水袋,但没有动,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再也倒不出任何一滴水了。
“可怜哪,堂堂京都府尹,曾是何等八面威风,一朝落马到了这步田地,还不如往常市井人家一饮一食来得悠闲自在。”
“老哥此话说差了,这卖国背主之人有啥好可怜的?谁叫他勾结契丹人对我大周图谋不轨?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罢了,圣上心慈宽仁,没将他满门抄斩,只判了个流充边塞,也算是他祖宗辈给他留了厚德吧。”
两名差官一老一壮,斜倚着枯树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间或拿眼斜觑一下几步开外的贺锦心父女俩。
那壮年差官忽地将眉目一转,压低了嗓音说道:“哎老哥你说,这一大家子自开路以来,一路上死了个七七八八的,可这老东西却忒是命硬,要死不死的竟然拖到今日,还有这小娘们……”
声音越来越低,逐渐变成了耳语,两名差官交头接耳不时发出一两声干笑,又很快被风沙带着传入贺锦心的耳朵里,令贺锦心的心头不禁一凛,警觉地抱紧了怀中包袱。
这时父亲贺钰捂着胸口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一丝暗红的鲜血从嘴角缓缓淌出。
“父亲……”贺锦心呼唤着,忙用衣袖为父亲擦试。
贺钰轻轻摇了摇头,沙漠正午的阳光打着一轮又一轮的光圈直射在他的脸上,愈显得苍白老态,生命已剩下最后的一缕游丝。
两个月之前,贺钰还是大周京城汴梁府尹。
都说京城的府尹最是难当,而贺钰生性忠厚耿直、嫉恶如仇,且由于他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在京城之中倒也赢得赫赫官声,朝中大员、皇亲贵戚们见到他时都客客气气礼仪有加。
当然,得罪人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清河潮汛急危,朝廷年年拨款整修河道年年失修,洪水泛滥成灾,民不聊生。
而贪墨大批治河钱款的正是当朝太傅杜彦。
铁面御史沈潭历时半载,掌握了大量证据,联合贺钰共同上奏弹劾杜彦,却不料最重要的证物在送往皇宫的途中被劫,证物再无处查起,原本铁板钉钉的案情急转直下。
翌日,那盗贼被人灭了口,横尸街头。
巡捕从盗贼身上搜出的,竟然是一份沈潭贺钰与北汉刘崇的使臣相互往来的手书,手书的内容为北汉意欲联合契丹人攻打大周,沈潭贺钰则做为内应。
沈潭贺钰弹劾杜彦不成,反而坐实了通敌背主的罪名,连同贪墨治河款的罪名通通倒扣在了他们身上。
白纸黑墨,字字都是沈潭亲手所书,二人百口莫辩。
“清河不清,浊流害民,奸人不除,愧对黎民。”
沈潭悲恨交加,当朝触柱而亡。
贺钰则落得个削官夺职,充军边关、抄家没产的下场。
除了大小姐贺锦衣正好在外拜师研习琴艺而侥幸逃脱之外,一家子老老小小十多人口全都象牲畜一般被驱使着往关外赶。
一家老小哪里受过如此磨难?刚刚出得关来,便一个个地倒下,三位夫人相继去世。
小妹贺锦颜眼看着也快死了,两官差一合计,趁着锦颜还未断气,竟然悄悄将她卖与一位到关外贩皮货的徽商,锦心发觉追出去已不见小妹踪影。
原本十多人口,只剩下贺钰与次女锦心父女俩苟延残喘,强撑勉行。
一路风餐露宿的艰辛自不必说,在两个官差紧催慢赶大呼小喝中艰难跋涉,好不容易捱到了边城,眼看着离役营不远了,越过沙海就算是到得地方,贺钰却是一病不起。
锦心日夜照看父亲,也是精疲力竭。
“官差大哥,我父亲病得不轻,实在不能继续行走了。况这里已是边城,离役营也是不远了,就让我父亲歇两日吧?”
“不行,得快些去役营交割了,我俩好赶回京城,家中老小还等着一起过年。你当自己还是府尹千金大小姐呢?在这指手划脚?”
“我说千金大小姐呀,也不是我俩不通情理,你看这天儿指不定哪日就该有风暴,到时候沙海过不去,岂不又耽搁了许多时日?”
年长的一位官差看着一老一小,有些过意不去,说些道理给锦心,总之还是逼着他们赶路。
这两位官差掐着指头算着回京过年的时日,一日都不肯迁延,逼着锦心搀扶着老父,哆哆嗦嗦地进了沙漠,却不想这一脚便踏进了鬼门关半步。
他们刚入沙海就刮起了暴风,退出来已来不及,渐渐地迷了方向,原本五、六日的路程,在沙海里兜兜转转逡巡了十多日还没有走出去,而粮食和水也已断绝。
贺钰一个书呆子哪里受过这般苦楚,熬了几日眼看就要熬不住了。
“父亲,这一大家子都没了,小妹被不良差官卖了,大姐也不知流落何处,您可不能再丢下女儿一个人啊。”
锦心守着父亲悲鸣,望断南飞雁,只恨自己空有一身三脚猫的武艺却没法弯弓引射。
“锦心我儿,为父害苦你了。”
贺钰满是皱纹的眼角落下一滴老泪,望着女儿悲伤的脸,想抬手抚摸,终究无力地垂下,气息奄奄。
贺家无子,三位夫人各生一个女儿,大小姐锦衣天姿国色,擅长琴艺,三小姐锦颜年纪尚小,乖巧可人,最会卖乖,在父亲身旁修习诗文。
唯有二小姐锦心最不安分,女儿家家的偏喜刑律断案之事,常常假扮府中捕快跟随父亲身边,顺便也跟着府中捕快们学些拳脚剑式。
捕快们都只当她是玩笑,唯有捕头桓靖大哥尚肯认真教她一招半式的。
只是她学起来四不象,桓靖大哥笑她的掌式为“绵绵掌”,空有架式,而没有半点杀伤力。
贺钰每日从府堂回来便与两个女儿吟诗弹琴作乐,再看看二女儿耍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倒也其乐融融,颐养天年。
却不想有朝一日突然遭此飞来横祸,落得个戚戚然家破人亡。
“想我贺家世代书香门庭,终是断送于我这无用之身。若不是证物被贼人所劫,莫名被指勾结乱贼,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境地?杜彦奸贼犯科,害我忠良,此恨难消。皇天不公、不公哪。”
“父亲且再坚持片刻,穿过这片沙海就快到役营了。”
贺锦心宽慰父亲也是宽慰自己,而茫茫沙海哪里是尽头?
“证物、证物……”父亲的手渐渐地垂下,而他那没有血色的双唇歙动着,只重复这两个字。
贺锦心眼看着父亲气若游丝,于悲苦之间抬起头来,却发现两个官差在一旁鬼鬼祟祟地小声嘀咕,眼神时不时地往贺钰身上瞟。
不禁心头一凛:这两个恶差莫非要起歹意?
果然两个官差各持一把钢刀一前一后向贺钰与锦心包抄了过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说,这府尹老爷就快咽气了,而我们缺水少粮的,不如就成全了我们,否则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鬼沙城。”
“休得无礼。”
贺锦心心中惊恐,两位恶差竟然想要杀人喝血吃肉,锦心又怎肯让他们伤父亲分毫?
锦心迅速起身,双掌呈剪刀之势,守着父亲是寸步不让,与两个恶差对峙着,生死关头,双方都红了眼,一场恶斗即将爆发。
贺锦心已经多日滴水未沾,饿得前心贴后背,实力悬殊可想而知。
但她毫不退缩,有如沙漠中一只小豹,为了保住父亲,就算只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也无论如何要与两位恶差拚个你死我活。
她是相当虚弱的,但苍白的脸庞上满满的却是无比的倔强,一边护住父亲,一边提着丹田努力支撑着自己决不倒下。
她机警地将眼睛瞟向那两把步步逼近的钢刀,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倒映出两张丑陋邪恶的脸庞令她觉得有些恶心,同时咬了咬嘴唇暗暗下了夺刀杀人的决心。
正相持间,忽地远处一阵马蹄声急,夹杂着嘈杂的呼哨声,同时箭翎呼啸而至,一支正中一名官差的心脏,一支射穿另一名官差的喉咙。
两人尚且站了片刻才扑身向前倒在沙海之中,目光幽幽正与贺钰相对。
“锦心我儿……”
贺钰叫了一声,瞪圆了双目,叫声被剧烈的咳嗽声打断。
锦心挂念父亲安危,急忙回过身去,却没有防备身后一个马鞭飞来给她沉重的一击,头重脚轻,堪堪栽倒在父亲面前。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被一个奔马而来的人提了起来倒挂在马背上。
“我的父亲,求求你们救救我的父亲。”
贺锦心艰难抬头,哭求救命,但那个人只是拍马在贺钰的身旁绕了一圈,并未有停留的意思。
贺锦心努力地伸手,却够不到父亲,只见父亲双目紧紧望着她,渐渐失去了光泽,张着嘴,叫不出声。
那人摇了摇头,打了个呼哨,策马而去。
“父亲,我的父亲啊,求求你们救……”
贺锦心的话音未落,群马已经飞奔,倒悬着的脸冲着满地黄沙,只看见父亲的身躯被飞扬的沙海掩埋,渐渐地隐没在视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