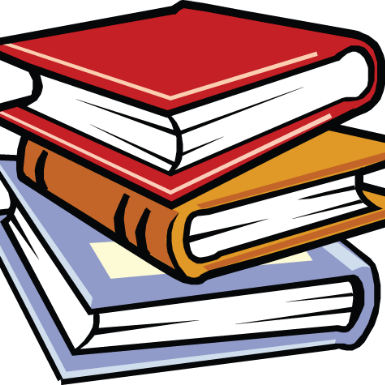李成因为能请到纪云舒来帮自己破案,甚觉自己脸上有光。
走路都带风。
加上此时一身官服,就更显威风。
待到了验尸房外时,他还刻意抖了下衣袖。
老官立刻上前:“李大人。”
“嗯。”
“这二位?”老官看着他身后的两个人。
有些困惑。
李成则咳了一声,指着纪云舒,隆重的介绍起来:“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位高人!她不仅能摸骨画像、还原死者生前相貌,还能巧破奇案。本官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请得她过来帮忙。”
说时,还微微抬了下下颌。
以此加重语气。
纪云舒小步移前,抬手与众人作了一礼:“在下姓纪,谈不上什么高人,只是一名懂得命脉的画师而已。”
李成立刻道:“纪公子,你用不着如此谦虚,你的厉害之处,我都与他们说了。”
大嘴巴!
纪云舒:“……”
大伙的目光一一落在她的身上,多是带有怀疑的。
因为在他们认为,与死人打交道的多是些粗脏的汉子、且上了些年纪的人,哪有像纪云舒这样如此白净的?
一看,分明是个文弱书生。
验尸破案?
当真不是开玩笑吗?
但没人敢当着李成的面说出自己心中的困惑。
随即,李成打算介绍景容。
可话刚到嘴边——
景容沉着脸,冷漠道:“不必了。”
那种冷,比此刻寒风还冷。
李成咽了咽口水,只好作罢。
这时,在旁的老仵作上前来,与纪云舒说:“纪先生是吧!李大人之前就提起你,说是死者的情况你也知道。”
“老先生是?”
“我是这司部里的仵作。”
“哦。”纪云舒朝他拱手。
“先生客气。那里面的骷髅头我已经验过了,死者是个十五左右的姑娘,死亡时间是三年前,和你告诉李大人的一样,但是……先生断定死者是被淹死的,这点不知从何而来?”
她直接说:“看出来的。”
“看?死因怎么能看得出来?先生可不要随口胡说。”
火药味浓重!
老仵作显然是想拆她台的。
纪云舒淡定的说:“若是没有十全的把握,晚辈又岂敢在老老先生面前胡说?”
老仵作一顿。
刚要再说些什么——
纪云舒就朝验尸房看了一眼,问:“东西都在里面吗?”
李成抢答:“都在。”
她点了下头,转而与景容说:“你在外面等我吧。”
景容颔首:“有事叫我。”
“嗯。”
她便进去了。
城司部的人也都好奇的很,一一围在门口看。
老仵作和李成则跟了进去。
那老仵作倒是要看看,李大人口中所说的高人究竟有多高。
纪云舒进去后,就径直走到被白布盖着的骷髅头边,从袖中拿出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手套戴上。
将白布掀开!
那颗骷髅头并没有什么变化,安安静静的躺在冰冷的板子上。
她拿起骷髅头左右仔细看了会。
手指在枕骨、鼻骨、下颌骨等几个重要的位置上轻轻按了几下。
心里有了个方向。
老仵作见纪云舒验骨的动作很熟练,有模有样。
但他还是有些怀疑。
他当了仵作这么多年,整个高定,甚至整个胡邑,大概都没人比他还厉害,怎就凭空生出一个这等奇人?
不信!
就是不信!
便出声问:“纪先生,怎么样了?看出什么来了?”
纪云舒抱着头颅,沉了沉声,肯定道:“死者确实是淹死的。”
“哪里可以看出来。”
“一个人的死因会直接导致人骨的变化,死者若是正常死亡,死后多年的骨骼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若是非自然死亡,比如烧死、上吊死、淹死、摔死等等,都会导致死后骨骼出现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
“你是说,人死后,骨骼还会变?”
“怎么?老先生不知道这点?”
“不是不知道,是从未听过这荒谬的说法。”老仵作不屑的笑了一下。
纪云舒汗颜,说:“老先生,你未听过,但不代表没有?晚辈因常常与死者的骸骨打交道,对人骨构架略有研究,故而知道这些,先生是仵作,验的是心肝脾肺肾和脑,不清楚也实属正常。”
“你……”老仵作哽了一下,说,“好,那你说说看,究竟死者头颅上有什么变化,让你断定她是淹死的?”
纪云舒每次验尸,总免不了与人解释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
这次也不例外。
老仵作问出了这个问题,正是大家心里想知道的。
一个个都盯着她。
李成更是往她身边靠近了些,好能听清楚点。纪云舒说:“人若是被淹死的,死后骨骼变化最大的就是鼻骨和下端的上颌骨,首先鼻骨会往上挪移,导致两边的额突挤压到泪骨,因为产生细纹状的崩裂现象,死者的额突和泪骨这段距离上正好有这种现
象发生。其次,就是上颌骨,淹死者,上颌骨朝鼻骨微有移动,导致原本呈圆端的梨状孔紧缩变形,凹而不平!这些,都在死者的头颅上体现出来,可用肉眼所见。”
大伙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都什么跟什么?
不懂!
而——
站在外面屋檐下的景容也听到了纪云舒的话。
他却面色担忧!
因为纪云舒越是如此出挑,招惹而来的就会越多!
相对于他,李成则像个花痴。
目不转睛的盯着纪云舒。
他知道纪云舒是女子之身,但一直都没有说破。
心想,要是能将她娶回家去,简直就跟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而老仵作更是完全怔住!
他当了几十年的仵作,什么奇奇怪怪的尸体没见过,没有上千,也有上百,却从未对人骨有如此研究,以至于纪云舒在说这些时候,他即便努力去听,到底还是一头雾水。
便问:“你说的这些……可有凭证?”
“老先生若是不信,大可去找一个正常死亡者的头颅来做对比就是,看看我刚才说的这两点究竟是子虚乌有?还是真凭实据?”
纪云舒都敢这么说,自然不怕他人来验证。
老仵作脚步挪了挪,不再固执。只得暂且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