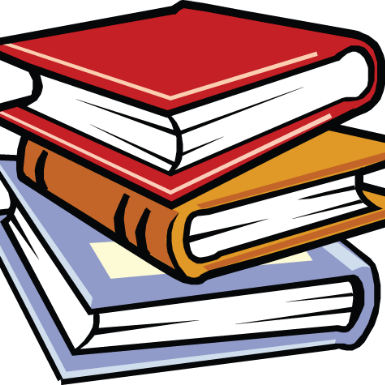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第一百三十六章番外9==
此时三更已过。
陆宴迟迟未醒,靖安长公主心有不安,便叫了大夫进来。
大夫将手搭在陆宴的手腕处,靖安长公主一脸凝重道:“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晕倒前,我瞧他捂了下心口。难不成是患了什么心疾?”
半晌过后,大夫收了手,轻轻摇头道:“世子身体康健,老夫并未看出什么不妥,许是......”
“许是什么?”长公主着急道。
大夫道:“许是太过喜悦所致。”
靖安长公主蹙眉道:“那他何时能醒来?”
这话一落,榻上的男人就缓缓睁开了眼。
见此,靖安长公主不由了一口气,无奈道:“你还知道醒过来?”
陆宴捂着胸口坐起身子。
眉宇紧蹙,双眸深邃,他看着长公主,疑惑道:“阿娘?”
长公主轻嗤一声,“你可真能耐,陆时砚你全长安打着灯笼去找,也找不出在前脚得子,后脚便昏过去的男人!”
这可真是......
陆宴半晌未语。
得子?这是何意?
“你若是无事,就去看看她吧。”长公主扶了扶额头。
嬷嬷在一旁道:“这都折腾了一个晚上了,既然世子身子无恙,那长公主还是早些休息吧,”
长公主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我是该回去歇息了,走吧。”
长公主走后,男人摸了摸胸口,直接脱了衣裳。
他的胸口,为何没了箭伤,那两处疤呢?
这时,婢女正好进来送药,一推门就看到了男子精壮的背脊,药盏“啪”地一声碎落在地,“奴婢重新去熬,奴婢这就告退。”
陆宴回眸,冷声道:“杨宗呢?”
婢女不敢抬眸,老实道:“杨侍卫在外头。”
陆宴道:“叫他进来。”
未几,杨宗提着嘴角迈进了屋子,“主子,您总算是醒了!”杨宗想了想,躬身行了个大礼,道:“恭喜世子喜得麟儿!”
陆宴身子一僵,棱角分明的喉结缓缓下滑,“杨宗,今夕是何年?”
杨宗道:“主子方才说什么?”
陆宴凛声道:“今日,是何年何月!”
杨宗道:“元庆十九年,正月二十八。”
陆宴跌坐在榻上,双手放于膝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
元庆十九年......
这不就是他毒发的那一年吗?
思及此,陆宴不禁抬手揉了揉眉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有个孩子,谁的孩子?
杨宗低声道:“主子,您不去看看夫人吗?”
陆宴抬眸,疑惑道:“夫人?”还有个夫人?
这下杨宗都些懵了,他讷讷道:“是啊,夫人还在等您呢。”
陆宴下意识道:“你说的许七娘?”
说到此处,杨宗的眼睛瞪地如同见鬼一般,低声道:“世子爷,您说什么呢!什么许七娘!您要不要把白大夫请来看看?这话若是叫夫人听见......”
陆宴直接打断道:“她在哪?”
杨宗道:“北苑刚清理出来,夫人还在里头。”
“我去看看。”陆宴冷着一张脸,想着与其在这听,还不如亲眼看看。
陆宴穿了衣裳,披上大氅,走出肃宁堂,大步流星地绕过结了冰的池塘,雪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站在北苑之外,定住,深吸一口气。
他侧过头,颔首对着一个婢女道:“进去通报一身。”
婢女一愣,“是。”
站在他身后的杨宗眼珠子都要掉了。
世子爷进夫人房里,何时让人通报过??
须臾,婢女躬身给他开门,陆宴跨进门,抬眸,全身的血液在刹那间沸腾,他喃喃道:“沈甄?”
你不是离开长安了吗?
陆宴看着沈甄垂眸逗弄着身边的婴孩,眉眼带笑。
“世子爷醒了?”棠月端着热乎乎的帨巾站在门口。
沈甄循声望去,刚好看到陆宴负手站在门口,冷着个脸。
“郎君。”她喊。
陆宴呼吸一窒,有些不敢去看她,他转了转手上的白玉扳指,明明想同她说句话,却如近乡情怯一般不敢上前,不敢开口。
“你愣着作甚?”沈甄看着他,朝他招了招手,“快过来呀!”
陆宴缓缓地走了过去,坐到了她身边,低头去看还未睁眼的孩子,怔怔道:“名字起了吗?”
沈甄蹙眉失笑,“陆大人今儿这是怎么了?”
陆宴与她对视,沉沉开口:“怎么?”
“他的名字,是你起的啊,陆昶安。”沈甄伸手去戳他的下颔,“”你怎会不记得?”
陆宴落在膝盖上的手空握了一下,缓缓道:“是我睡昏头了。”
沈甄单手扶着床沿,身子前倾,贴上他笑道:“我这个生孩子的都没昏,郎君怎么还晕过去了?”
陆宴看着凑过来一张娇靥,下意识亲了下她的额头,道:“你好似胖了些。”
话音甫落,沈甄的脸色立马就不好了。
美眸中尽是哀怨。
陆宴凝着她撂下去嘴角,抬手捏了一下她的脸,哽声道:“你胖点才好看。”
“显然刚刚那句才是心里话。”沈甄侧头看着闭目不动的陆昶安,“阿娘说郎君你小时候和他一样,你觉得像吗?”
他低声喃喃道:“阿娘说像,那便应该是像的。”
“要不要抱一下?”沈甄对他道。
陆宴道:“给我?”
“那不然呢?”沈甄轻声道:“你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甄指着陆昶安道:“郎君觉得他好看吗?”
陆宴看了一眼,直接道:“好看。”
陆宴将孩子抱在怀中,看了好久,沈甄伸手抚了抚他的眼底,道:“是不是近来太累了?”
陆宴招手叫来一个奶娘,把孩子递过去,回头对她道:“今日你辛苦,早些休息。”
旋即,沈甄就见陆宴把身上的大氅脱了下来,“郎君今日不回去吗?”
陆宴拉住她的手,“在这陪你。”
沈甄亲了亲他的下巴。
烛火熄灭,二人躺下,沈甄累了一天,靠在他的肩膀上,很快就睡着了。
寒风吹打着窗牖,怦怦作响,他给她掖了掖被角,耳畔忽然响起了她在去漠北之前说过的话。
“大人,我听闻漠北的天很蓝,云很低,触手可及,我,想去看看。”
“侯爷待我极好。”
“同大人在一处,起初并非是我本意。”
......
思及此,陆宴侧头去亲她的耳垂,默念:沈甄啊,这若是真的,该有多好?
她往他怀里躲,低声哼唧了道:“大人,我困了。”
听到着熟悉的称呼,男人在一片漆黑中勾起了嘴角。
她唤他郎君。
替他生下嫡子。
这一切,大概就是一场梦吧......
陆宴揽过她的腰,沉沉睡去......
******
翌日一早,陆宴睁开眼,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坐起了身子,环顾四周,身边空无一人。
忽然想起甚,他翻身下地,对棠月道:“夫人呢?”
棠月愣愣道:“奶娘在喂奶,夫人跟过去了。”
说罢,棠月给陆宴递了一杯水。
他抿了一口,放下,没过一会儿,沈甄掀起幔帐,抱着孩子,朝他走了过来,“你醒啦?”
陆宴起身,先看她,又看孩子。
“眼下还是冬季,你又刚生下孩子,怎的穿这么少?”
“不少了。”
“你听话。”
“再穿我都要走不动了......”
未几,沈甄碰了碰怀里的小手,道:“我怎么觉得他比昨日好看了些?”
陆宴勾了下唇角,不屑道:“才一天,你能看出什么来?”
沈甄横了他一眼,“可你昨儿还说他好看呢。”
昨日?
陆宴一怔,脑海中不由闪过几个画面,抬手捂住额心。
见状,沈甄担心道,“你最近是怎么了?”
陆宴摇了摇头,“我没事......”
傍晚时分,陆宴与沈甄从北苑搬回了肃宁堂。
二人如往常一般,盥洗过后,吹了烛火,一起躺下。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过了三更天,陆宴才生了睡意,垂垂阖眼时,眼前再一次出现了浓浓的黑雾......
===================
元庆十九年深秋,镇国公府挂起了素白色的帐纱。
靖安长公主跪坐在百安堂中央,绝望地佝偻着,掩面而泣,鬓角的乌发一夕之间白了大半。
长安的权贵们一一登门吊丧。
谁也想不到,大晋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宰相,就这样悄无生息地病逝了......
杨宗在肃宁堂收拾着东西。
按照陆宴临终之托,杨宗需要将这屋内的一切物件都搬出去,免得惹长公主伤心。
收拾字画时,杨宗翻出了陆宴留下的那封信。
上面写着,时砚亲启。
三年来,杨宗从不敢在陆宴面前提沈姑娘,可事到如今,已然无所谓了。
杨宗拆开了信件,缓缓打开,看完之后,眼眶不由一红。
心里突然像是横了一堵墙。
他在肃宁堂静坐一夜,想了又想,终是自作主张,将这封信放于烛火之上,烧成灰烬。
一阵风起......
时砚亲启——
参商流转(1),天涯人远。郎君览信之时,妾身或抵漠北。
意长纸短,举笔难落。幽思满腹,往事萦怀。
君眉间喜怒,犹在眼前,不知见字之时,展耶蹙耶?
昔年沈家之祸,恍惚在目,夜魇晨惊,历历如昨。
枯巢即覆,雏卵难全。
妾心中明白,妾与手足得安,皆为君之所顾。
穷途困窘,妾无以为报,量君不弃,曾欲为篷贱,就此侍君左右。
后悉君与许家七娘文定之喜,便知前望成空。
妾知这一切非君本意,却也知天命难违。
经此一别,妾愧怍无穷,结草衔环,难报万一。
此外,妾还有一事,想说与君听。
妾曾夜赴南柯,梦中种种,恍如隔世,人事衮衮,殊异于今。
迷雾之中,妾睹君未及而立便入中枢秉政,成一代贤臣。璋瓦双全,子女绕膝,名唤昶安、静姝。
憨声娇笑,音尤在耳。
虽知不过一枕黄粱,却使人有庄生之惑。
烟云过眼,往事成尘,后会不可期,君以时自重。
若有来生,愿君能似梦中那般,眉眼带笑,万事顺意。
沈甄谨却。
(梦境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