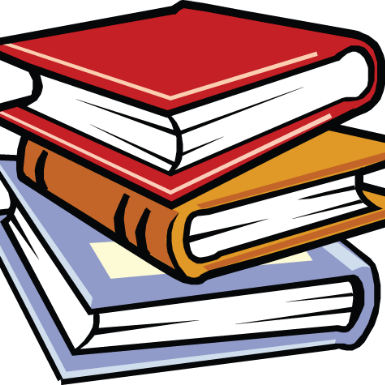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写完了《高老庄》,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这一部《怀念狼》,还在写《高老庄》时就谋划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两千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是人间天堂。
想到了一位画家,是西方的莫兰迪,有文章说他几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面对了几个罐子作画,画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检点起我在《高老庄》写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这样的试验能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我暂且不知,但写作中使我产生了快慰却是真的。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画家贾克梅第是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一九二五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怀念狼》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
在《高老庄》的后记里,我主要谈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写作人传达出的精神,现在我们十分看重它。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二十世纪末,或许二十一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有着它的民族性,即独特于西方人的思维和美学。诚然美国及西方的文化风靡,或许有一日全球统一化,但这一日对于中国来说毕竟不是短的日子。
《怀念狼》彻底不是了我以前写熟了的题材,写法上也有了改变,我估计它会让一些人读着不适应,或者说兴趣不大。可它必须是我要写的一部书。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纪里,文坛毕竟是更年轻的作家的舞台,我老了,可我并不感觉过气。《怀念狼》是我新千年里的第一本书,在即将脱稿的时候,到处是庆典的活动,有记者来采访,需要我谈谈感想,我并未因逢上了两千年而欢喜若狂,我说,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吧。写完了《怀念狼》,下来肯定又得去充电去谋划去写作了,只祈望着在以后的岁月里,杂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