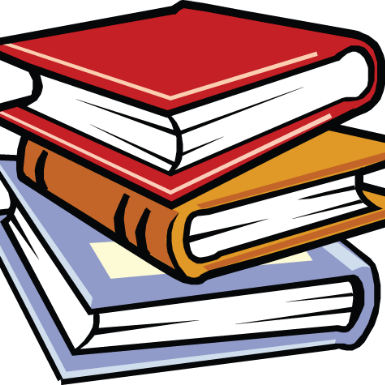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宾馆的服务员告诉说,那个山里人呢,会不会去寻公共厕所了,他说他坐在马桶上拉不出屎来。)
天近傍晚,舅舅回来了,我进房间的时候他正在洗手间小解,还低头看着自己的东西,听见门响,忙双手捂了下身转过身去,惊慌失措的样子犹如一个害羞的女人。我问他到哪儿去了,他说他是去了沙河子。
沙河子在州城东十五里地,一条沟川,盛产花生,捕狼队两个队员的家就住在那里。“噢,”我说,“老朋友相见肯定愉快了!”可舅舅的神情并不好,还挽起衣袖,左手握握右手手腕,又用右手握握左手手腕,并过来握我的手腕,说:你的比我粗。其实我的手腕并没有他的手腕粗,而且他的手腕非常有力,可舅舅坚持在说我的手腕比他的手腕粗壮。我只好说:搞摄影除了是脑力活外更是体力活,整日扛机子,练得手腕粗了吧。
“我以前的手腕是一把握不住的……”他说。
我真傻,并不明白他的意思,还以为他是为无聊而情绪低落的胡言乱语,就告诉他流星雨的事。这个晚上我们守在鸡冠山顶的平台上,远近就我和舅舅,还有富贵,没有风,也没有雾。不远处就是州城的电视插播站,一间小屋外的铁塔上亮着一盏灯,光芒乍长乍短,愈发使夜黑得如同锅底。舅舅并不知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只说了“你还会看天象呀”就提议他是不是去找些柴火来燃一堆篝火,又说你听你听,听见有什么叫吗?我并没有听到什么,他摇了摇头,又问我闻见了什么,他说这山上有狐狸的,还有黄鼠狼哩,这么大的骚屁味儿你闻不出来?我才说了一句我有鼻炎的。突然在东北方向,有成千上万颗流星呈扇面通过我们的头顶向西南部迅速滑动,像是倾注了一阵暴雨。刹那间一片灿烂,却什么也都看不见,我感觉里星雨劈里啪啦地砸向了自己,在地上砸出无数的坑儿,哧溜哧溜地冒白烟儿,或许那一股白光像卷过来的龙卷风,要裹挟着我也飞去了。我大呼小叫,按动了摄影机快门,一块石头在脚下绊倒了我,我跌坐在地上还是拍照,一直到流星雨完全结束,一切又陷于了黑暗里,才发现舅舅没有哼一声,富贵也没有汪,则全然瘫坐在地上,如痴如呆了一般。
“舅舅,”我说,“你没有看流星雨吗?”
“你就领我来看这个的?!”“这可是千年不遇的奇观!”“千年不遇?”他紧张得有些发抖,“天上掉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的,这么多的星星在落哩,这是要发生什么灾难吗?”
“这是天文现象,与灾难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天上下雪,你不觉得冷吗?!”“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怀疑白天舅舅在沙河子有了什么事了。
回宾馆的路上,满城的高大建筑物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都在看流星雨,甚至还盼望着新的一阵流星雨落下,有人带着啤酒边看边喝,流星雨已经过去了,酒还没有喝完,瓶子就摔打在楼下的空地上,而有人在开始放鞭炮,爆竹放射着绚丽的火花在空中反复明灭。我和舅舅一边走着一边仰头朝建筑物上观看,生怕有空瓶子和爆竹落在我们头上。舅舅终于告诉我,白天里真的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沙河子住着的两个队友,一个害了头痛病,头痛起来就得用拳头捶打他的脑袋,捶得咚咚地响,看过了许多医生,却断不清病因,只是每日服三次芬必得,阴阳先生说这是有了孽障了,让他用木头刻一个脑袋,一犯病就拿锤子、刀子在木脑袋上砸、刻、戳。
多壮实活泼的人,用锤子一边砸木脑袋一边就流泪了,说:我这是在地狱受刑了,受的是千刀万剐的罪啊!一个患上了更可怕的病,浑身的骨节发软,四肢肌肉萎缩,但饭量却依然好,腰腹越来越粗圆,形状像个蜘蛛,现在双腿已经站不起来了。
“我发觉我手腕也是比以前细了,”舅舅喃喃不已。远远的一座高楼上放射了一个二踢脚的鞭炮,日地一声从空中划过弧线掉在我们面前,爆响了。舅舅又哆嗦了一下。“是细啦,真的是细啦……”舅舅的样子很可怜,也真有些神经兮兮,我说手腕那么粗的,细了什么呀?!他倒生气了。他一生气,我也不再言语,举了相机在街上拍照起来,他却撵着给我说话。
“子明。”“哎。”他又是不说了。
“瞧那一排房子多有特点,是清代还是明代的建筑?”
“你不会笑话舅舅吧?”
“我怎么会笑话你?”
“那我给你说了吧。子明,我那瘫了的队友对我说,他是翻过一本药书了,上面写着因手淫过度或因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所患的怪病。那病的状况与他的病很相似,舅舅不怕你耻笑了,舅舅在打猎的时候也是曾手淫过。猎人在野外有过手淫的。
舅舅思想不好,怕是手淫多了,舅舅也就得上了这种病的。”他的话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再没有生硬的指责,也没有了戏谑的言辞,严正地劝慰道:“哪儿会有这种病呢,你的那个队友一定是同所有猎人一样,自从不能打猎了,没有狼了,失去了对手,就胡思乱想脑子生了病。病有一种是想出来的,想着要生病了,生病了,或许就真的生病了。舅舅身体这么好,怎么能患那种病呢?就说手淫吧,凡是男人,哪一个一生没有过手淫的经历呢?以科学的观点看,手淫本身对身体无害,手淫对身体的害处是老以为手淫对身体有害。”舅舅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你是知识分子,你可不敢哄舅舅。”“我怎么会哄了舅舅?!”
舅舅终于给我笑了一下。他笑得很羞怯,这是我这么多天里没有见过的。
回到宾馆,舅舅睡着了,或许是跑动了一天累了,或许是相信了我的话,靠坐在床头睡得很沉,涎水把前胸都流湿了。我却睡不着了,我有在深夜和黎明醒来之时逮听声音的习惯,我崇拜世间的声音,总以每日听到的第一声音来预测这一天的凶吉祸福,但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猎人们普遍患了软脚病,他们认作是没有了狼之后的灾难的降临,狼和他们是对应着的,有了狼就有了他们,有了他们必是要有着狼的,狼作为人类的恐惧象征,人却在世世代代的恐惧中生存繁衍下来,如今与人相斗相争了几千年的狼突然要灭绝,天上的星星也在这时候雨一样落下,预示着一种什么灾难呢?猎人们以狼的减少首先感到了更大的恐惧,而我们大多数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当流星雨发生,却仅仅以为遇上了奇观而欢呼雀跃,这是舅舅他们神经质了呢还是我们身心麻木?!我尊重起了我的舅舅,觉得这次跟舅舅相见,一定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的事。人在世上,做什么职业,有什么品行和技能,那都是依定数来的,如家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需要有一把茶壶,我们就才去街上的商店里买茶壶,有了茶壶就得有茶碗呀,于是又去商店买茶碗。见到了舅舅,我将不仅要拍下十五只狼的照片而出名,还要以舅舅的故事来撰写一篇关于人类灾难感应的报告了。
天亮的时候,我出去散步,街道上许多人在慌乱地奔跑,有一个妇女披头散发,一边跑一边哭号:“小曼,曼曼,我的孩子!”身子就软得趴在地上,已经跑到前头的人又折回来拉她,拉不动,几个人架着胳膊把她抬着又往前跑,妇女的一只鞋就掉下来。我捡起了那鞋,问旁边的人:怎么啦,怎么啦?回答说:不得了了,死了人了,死了十二个女学生了!我提着鞋去撵他们,前边的小巷里就一排儿拉出了十二辆架子车,车上分别是一具具尸体,尸体上盖着白布,但白布太小,上边盖住了头,而下边的脚却露着,围着车子的是呼天抢地的死者家属。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正是上班时间,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一时交通大乱。
我一直是跟着那个掉了鞋的妇女的,我挤到了架子车边,我并没有看到十二个尸体的全部样子,但那妇女揭开了第三辆车上的白布,她就昏倒了。车上果真是一位花季少女,头发很长,梳着马尾巴状,留海上还别着一枚白蝴蝶卡,脸蛋完好无缺,但下身却满是血,以至于袜子和鞋全被血浆糊住。我听见周围的人都在说,这些孩子昨天晚上相约了去鸡冠山根的一个草地上看流星雨的,流星雨使她们兴奋异常,流星雨结束之后她们还在草地上歌咏和嬉闹。整整一夜,孩子们没有回家,她们的家长就着急了,四处寻找,黎明时分才发现她们全死在了草地上,她们的身上没有钝器的伤痕和勒痕,但下身却全部稀烂,甚至屁股上也没了肉。“她们是遭到强暴了,”人们在议论着,“可强暴不至于下身被挖了肉呀?”有人就叫了一声:“怪了,莫非是被狼坏了的?!”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了奶奶曾经说过的一个久远的故事,说是老城池的某人夜里独自行路,一只狼就一直跟着他,他知道不敢停下来与狼搏斗,搏斗是搏斗不过的,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但狼就在他的屁股上抓,抓下了一块肉,又抓下了一块肉。那人咬着牙还是走,走到城池外的十字路口,前边有了人的说话声,狼是跑走了,他却一下子倒在地上,摸摸屁股,半个屁股上已经没肉了。
但是,州城里怎么会有狼呢,就是有狼又怎么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狼,将十二个少女的屁股抓得没了肉呢?人们怀疑着这种说法,但人们又都如此地传播着这是狼干的勾当,除了狼还会有谁呢?而有人就突然说了一句:“前几日我看见一只狼抬进城了,抬狼的人说不定都是狼伪装的,现在的世上什么事会没有?!”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忙退出人群跑回了宾馆,但我在宾馆门口停留了好久,我不敢把街上的事说给舅舅,也不能让舅舅看出我的神色异样。
舅舅已经起来了,他坐在床上,使劲地在身上搔痒,他的情绪似乎不错,一边哼着小调一边竟当着我的面解开怀捉起虱子。
“你说世上先有人呢还是先有虱子?”
“虱子。虱子是最古老的虫子。”
“人也是虫子。”
“嗯?”
“人是走虫。”
“……”
“你说,狼呢,先有了狼还是先有了狗?”
“狼吧,狼也是古老的虫子。”“可狼是把狗叫舅哩。”我帮他把衣服脱了下来。
“舅舅,今日我去行署再看看施德他们,明日一早咱们就可以上路了,你在宾馆里就刷刷牙,冲个热水澡吧。”
“我才不洗热水澡的,刷什么牙,你刷牙哩,你一嘴的溃疡,狼一辈子不刷牙,它倒天天有肉吃哩!”我笑了,说:“那你就呆在房间,哪儿也不要去,等着我。”“我得去沙河子一趟。”“还去沙河子?”
舅舅给我点着头。
我虽然理解他,却不免为他还要去沙河子感到惊讶了。舅舅裸着上身,他的脊背和肩头上满是疤痕,竟在脖子上还挂着小小的一块石头。这些伤疤,不用询问,都是他作为猎人的历史记录,而他佩戴的小石头却让我有了一份好奇。早听说过出猎和出海的人一样是非常讲究迷信的,他们在山林里绝不说不吉利的话,甚至也忌讳“滚了”、“完了”的词,如果临出门时灯突然熄灭,或是过门槛时踢了脚趾头,打了个趔趄,那就会停止当日的行动,在他们的身上常要带着黄裱写成的护身符咒,或是枪毙人的布告上的红勾纸片,或是年轻女人的经血布带,一定要处女的。但舅舅佩戴的竟还有着一块石头。我附过身抓住那小石头玩弄,石头发黑,光洁温润,“哟,舅舅要做贾宝玉哩!”“这是块宝玉,哪儿会假?”他显然是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你闻闻你的手,是什么味道?”
我的手上有淡淡的一股巧克力味。和舅舅住在一起,我是偶尔闻到过这种气味,还以为是住在宾馆里,房间里喷洒了什么香味,原来气味来自这块石头。
“这是金香玉。”金香玉,是那句成语“有眼不识金香玉”的金香玉吗?舅舅说是的,我把小石头从他的脖子上取下凑在鼻前,香味更浓了。我突然想历史上有个叫香妃的,说是身上放有异香,人怎么能放出香味呢,莫非她佩戴了就是这么一块有香的石头?!可是,女人是佩戴金香玉的,舅舅,一个粗而臭的男人,佩戴的什么金香玉呢?这简直是一个遥远神秘的童话!但舅舅绝不是文人,他不会加盐加醋地想象,他告诉我石头是红岩观的老道士送给他的。老道士是和观里惟一的徒弟在深山的一个溶洞里偶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的,他们把石头装在麻袋里背下山,搭乘了当地进山拉木料的拖拉机。行至半路,老道士一阵恶心,就让拖拉机停了,他下去呕吐,呕吐了好长时间还是难受,开拖拉机的人就不耐烦,竟把拖拉机开走了。
老道士那时还有些生气,骂了一声,但谁能料到,开走的拖拉机在驶出两千米左右翻跌到了二十米高的崖下,拖拉机上的人无一生还,他的那个徒递连头都被压扁了。
老道士拣了一条命,他坚信是这块奇石拯救了他,就将石头拿回观里供奉在案头。
这块石头有奇处,观周围的山里人都是知道了的,却谁也说不清这是一块什么石头。
两年前州里召开全省的地质会议,老道士带了石头去找科学家鉴定,终于认定了这是金香玉。金香玉的出世当然轰动了地质界,但追问石头是哪儿来的,老道士不说,他明白这是上天赐与的缘分,“我送给你们一份吧”,于是石头一分为二,一半贡献了地质部门,一半带回观里,并在一个大雪天里悄然进山,想用乱石堵了那个溶洞口,奇怪的是洞口竟发生了塌崖,连他也寻不着了洞口的方位。老道士从此再不提这件事,但老道手里还有一半金香玉的事毕竟传播开来,省里州里的有钱人接踵而来,要拿黄金的六倍价来购买,老道士一口咬定全捐献国家了,而私下里将那一半金香玉锯成小薄片,分赠给了曾给观里办过事的人。舅舅是最后一次普查狼时到过那座山上,夜里就住在观里,他诉说着猎人将不能猎狼的恐惧,老道士便送给了他这块金香玉作了护身符。
“老道士还在吗?”我当然不能索要舅舅的护身符,但我太喜欢这样的石头了。
“还活着吧,”舅舅说,“如果咱们真能去为狼拍照,我可以领你去红岩观,能不能送你一块儿,那就看缘分了。”我相信我有这个缘分。我已经琢磨好了,一旦我能得到一块金香玉,我是不会交给老婆的,要送就送我的女朋友,让她成为我的香妃。但是,舅舅再次去了沙河子,当天并没有返回,甚至三天也没有人影。
乡下人的时间观念差,这是最令我头疼的,可他迟迟不回来,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州城图书馆借阅关于狼的有关资料,十分遗憾,狼的书籍太少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一下狼的习性和生存的环境以及发情、交配、生育的企望全然落空,我只是抱回了一堆有着狼的故事的小说。于是,重新读了《聊斋志异》的一些章节,读了鲁迅的《祥林嫂》,读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我是坐着读,窝在沙发里读,后来就躺在舅舅的那张床上读。
舅舅的床上是铺着狼皮的,我竟一时忘掉了狼毛会起的事,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上痒,目光刚一溜到狼皮上,发现狼毛都竖起来了,一下子吓得心都要跳出胸膛了,火烧似的从舅舅的床上跳坐到我的床上。坐到了我的床上,我一眼一眼盯着狼皮,宾馆里一片寂静,电灯白生生照着房间的四壁,总觉得那狼皮在动,心里告诫自己: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拿过书继续读,企图分散开我的恐惧。
可不去看,哪能又不去看?我闭着气站起来,哗啦一声将狼皮揭开,它毕竟是一块狼皮嘛。我说:我怕你什么,难道还附有了灵魂不成?!极快地打开窗子,我原准备把狼皮扔掉了的,但念及这毕竟是舅舅的东西,就将狼皮挂在了窗外,再关了窗扇,继续读我的书。书上写着山村的那个牧羊的孩子在喊:狼来了!狼来了!还没有读到山村里的人拿着刀棍向山上跑去,窗外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叫声,沉沉闷闷,但穿透力极强,像是我在省城听过有人吹起的埙音,接着有了狗咬,三声五声,再是七声八声,越来越杂,狂吠一片。服务员就敲我的门,问:“听见有狼叫吗?”
我说:“有狼叫?”服务员说:“我听见有狼叫了,前几日十二个女学生就被狼强暴了,这狼还在城里吗?”我大声地说:“你是胡说,你肯定是狼把学生强暴了的?州城里哪会有狼,谣言惑众你要负责任的!”服务员是一脸的疑惑,后来走掉了。
他一走,我却慌了,难道那叫声是我挂出去的狼皮发出来的?赶忙开窗把狼皮取回来,它不就是一张软软的狼皮么,可窗外的狗群吠声便渐渐歇退了。这一下,我真的害怕了,知道这张狼皮是附着了狼的灵魂的。我老婆就曾经说过,每一个蝴蝶都是死去的美丽女人的亡灵在寻找过去的,那么,狼死了灵魂和皮毛是分离的,今晚上游荡的狼魂是怀念了他的衣服呢还是来拜会一个要去给活着的狼拍照的人?我再也不敢睡去,瞪大了眼睛只盯着狼皮到天亮。狼皮却再没有发生任何异样的动静。
九点钟,我打问着沙河子的方位,一定要找到我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