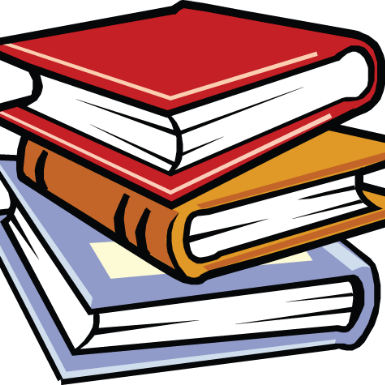慧仙坐在我家的舱里,坐在我父亲的海绵沙发上。这个小女孩烦躁,任性,贪嘴,吃掉了我家所有能吃的零食,还不罢休,赖在海绵沙发上,谁来拉她也不肯起来。这是我对慧仙最初的印象,不言而喻,这个印象是比较恶劣的。
说说那只海绵沙发吧。那沙发面料是灯芯绒的,蓝色的底,洒着黄色的向日葵花瓣,如果细细地察看,留有明显的公物痕迹,沙发的木质扶手明显被很多人的烟头烫过,背面材料是用的细帆布,帆布上“革命委员会好“的字样还清晰可见。向阳船队的船民,通常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我家的沙发很久以来一直是船队最奢侈的物品,它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孩子们的屁股。因此,我维护这张沙发的主权,维护得非常辛苦。船队的孩子为了沙发闯到七号船上来,他们或者婉转或者直接地向我提出要求,让我坐一次沙发,就坐一次,行不行?我一律坚决地摇头,不行,你要坐,交两毛钱来。
慧仙一上七号船,我对沙发的严格管理乱了套,我怎么能向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开口要两毛钱呢?所有的规矩都被她打破了。我记得那天她的小脸和鼻子紧贴着后舱的窗玻璃,在七号船上固执地搜寻着她母亲的踪影。我们家的后舱,是所有驳船上最零乱也最神秘的后舱,舱壁上有一幅女烈士邓少香的遗像,是从报纸上剪切下来的,邓少香的面容模糊,因为模糊,她的形象显得神秘而古老。慧仙隔窗研究着女烈士的遗像,突然说,那是死人!她信口开河,别的孩子吓了一跳,观察我的反应,我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她说的也没错,烈士都是死人,不死怎么叫烈士呢。然后慧仙发现了我家的沙发,她说,那是沙发,海绵沙发!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放着一本书,他抬头朝小女孩笑了一下,表示礼貌。外面好多孩子替慧仙表达她的要求,她要坐沙发,她要坐你家的沙发!我父亲站起来,慷慨地指了指沙发,你喜欢坐沙发?来呀,来坐。这邀请来得及时,慧仙抹抹眼泪,就朝后舱里冲下去了,大家都听见她的嚷嚷声,沙发,沙发,我爸爸的沙发!
我不知道慧仙是怎么回事,我们船上的沙发,为什么是她爸爸的沙发呢?那么小的小女孩,说话可以不负责任,我不跟她计较,心里暗自思忖,那女孩的爸爸,大概也是坐沙发的,不是干部,就是大城市的居民。我看见女孩像一只小鸟扑向鸟巢,轻盈地一跃,人就占领了沙发。外面的船民们不知为何鼓起掌来,他们窃窃私语,观察着我们父子的表现,父亲的表现早在他们的预计之中,他垂手站在一边,似乎一个年迈昏庸的国王,把宝座向一个小女孩拱手相让,船民们关注的是我的态度,慧仙堪比一块试金石,孩子们要考验我的公正,大人们则是要借此测试我的仁慈和善良。
起初我很公正,恶狠狠地去拉扯慧仙,手在空中抓了一下,差点抓到她的小辫子,不知怎么手一软,我头一次被仁慈和善良所俘虏,放弃了我的职责。我眼睁睁看着她跳到沙发上,一只脚翘在扶手上,身体非常熟练地沉下去,她的小脸上掠过满足和欣慰之色,这一瞬间,她一定忘记了母亲,我听见她用一种老妇女的口气说,累死我啦。过了一会儿,她瞄着柜子上的饼干盒说,饿死我了。我父亲赶紧把饼干盒递给她,她风卷残云般消灭了盒子里的所有零食,吃光了把盒子还给我父亲,饼干怎么是软的?不好吃。她朝我看看,闭上眼睛,又看看我,再闭上眼睛,几秒钟的功夫,一阵浓重的睡意就把她的眼睛黏住了。
我站在一边说,你把脚放下来,要坐就好好坐,别把沙发弄脏了,快把脚放下来呀。
她已经睁不开眼了,毫不理会我的要求,脚在扶手上踢了一下。我注意到她穿着一双红色的布鞋,布鞋上沾满了泥浆,我还注意到她穿了袜子,一只袜子在脚踝上,另一只滑到鞋底里了。我看了看旁边的父亲,父亲说,这小孩累坏了,就让她在沙发上睡吧。
我没有反对,回头看看舷窗外面,二福和大勇他们的脸正挤在玻璃上,一个在扮鬼脸,另一个还在咽口水,表情看上去愤愤不平。
小女孩慧仙像一个神秘的礼物从天而降,落在河上,落在向阳船队,落在我家的七号船上。这礼物来得突然,不知是好是坏,它是赠与向阳船队全体船民的,船民们对这件礼物充满了兴趣,只是一时不知如何分享。船队的很多女人和孩子想起有个礼物在船上,都莫名地兴奋,鱼一样在七号船上来回穿梭,很多脑袋聚集在我家的舱窗口,争先恐后的,就像参观一个稀奇的小动物。慧仙四仰八叉躺在我父亲的沙发上,看上去睡得很香。我要去给她拖鞋,父亲示意我别去惊动她,他从柜子上拿了一件毛线衫,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了,男人的毛线衫盖在她的身上,正好像一条被子,遮住了小女孩的身体。我走到舱门口,听见外面的女人交头接耳,正在表扬我父亲,看不出来,库书记还很会照顾人呢。见我钻出了舱房,他们又表扬我,说东亮表现也不错,这孩子外表凶巴巴的,心肠其实很软的。只有孩子们不懂事,都来与我较劲,男孩子鄙夷地看着我,想说什么难听的话,笨嘴拙舌的不会说,只有六号船上的樱桃,那会儿人还没有一条扁担高,嫉妒心已经很强,她把脑袋伸进舱里,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劈头盖脸批评我,库东亮你搞不正之风,我们要坐你家的沙发,坐一下都不行,她就能在沙发上睡,你怎么不让她交两毛钱呢?
我守在舱门口,顾不上和樱桃斗嘴,我注意到父亲在沙发边转悠着,像热锅上的蚂蚁,离开了沙发,他看上去无处可去。他注视着沙发上的小女孩,目光有点焦灼,有点窘迫,还有点莫名的腼腆。我看见他在我的行军床上坐了一会儿,在地上站了一会儿,局促不安,突然,他对我挥挥手,东亮,我们都出去,干脆把舱房让给她吧。
父亲终于走出了船舱,他从舱里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本《反杜林论》。
船民们很久没见我父亲出来了,终日不见阳光的舱内生活,使他的脸色日益苍白,与船上男人黝黑的面孔形成天壤之别。他一出来,船民们条件反射,一大堆人群退潮般的往后退。我父亲知道他们为什么往后退,他嘴里向船民们打着招呼,表情窘迫,眼睛里充满了歉意。父亲对王六指说,老王,今天天气不错啊。王六指斜着眼睛看看河上灰暗的天空,还不错呢,没看见河上游都黑下来了,马上要下雨的。父亲看了看河上游的天空,眼睛里的歉意更深了,是呀,我眼神不好了,那边的天已经黑下来了,恐怕是要下雨的。他对大人表示了热情和礼貌,怕冷落了孩子们,又去拍二福的脑袋,二福呀,好久没见,你又长高了嘛。二福缩起脖子从我父亲的手掌下躲开,忿忿地说,我根本没长高,吃不上肉,怎么长得高?父亲满脸尴尬,站在舱棚里,等着船民们开口向他问好,孙喜明总算对我父亲说了句关心的话语,库书记出来了?你是该出来透透气的,天天闷在舱下面,对身体不好。德盛女人的话听起来也受用,她说,库书记呀,都快不认识你了,外面放鞭炮也没法把你引出来,还是舱里的小可怜把你撵出来啦。
我在旁边明察秋毫。船民毕竟是船民,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眼神,眼神泄漏了天机。无论男女老少,目光都像一枚尖利的指南针,直指我父亲的裤裆部位,无论是好奇还是猥亵,所有人的目光都无情地探究着我父亲的裤裆。我觉得父亲像一个裸身的小丑,站在舞台的灯光里。父亲穿着一条灰色维尼纶的长裤,裤洞的纽扣扣得一丝不苟,周围褶皱自然熨帖,看上去一切正常。船民们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不甘心,很多人的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目光似乎要穿越维尼纶布料,亲眼见证我父亲半个阴_茎的秘密。他们还是看不见,看不见刺激了他们的想象,想象撕掉了一层遮羞布,我注意到王六指和春生互相对视一眼,两个人忽然挤眉弄眼起来。几个女人的目光含蓄一些,是跳跃式的,那些目光从父亲的下身一掠而过,跳到别处,跳到岸上,很快又热切地返回原处,我看见樱桃的母亲搂着樱桃做掩护,一只手捂着嘴笑,樱桃不解,扯她母亲的衣袖,你笑什么?樱桃的母亲就虎起脸打了女儿一下,你胡说什么,谁在笑?我哪儿笑了?
父亲脸色灰白,迎着众人乱箭般的目光,我看见他弓了弓腰,弓腰是没用的,他的羞耻无处可藏。我看见他的手慌乱地垂下,用《反杜林论》遮挡着裤裆,《反杜林论》也是没用的,一本书遮不住父亲的耻辱。我愤怒了。我的愤怒不仅针对船民的粗野,也针对我父亲的怯懦。我过去拼命把父亲往后舱门口推,你下去,快下去!我像父亲命令儿子一样对他喊,下去,看你的书去。父亲一定知道我的用意,他退到舱门口,尴尬地站到船棚的阴影里,我又去撵其他人,先推大勇,滚,滚开,别在我家船上,你们为什么非要赖在我家船上?推了大勇我又推他妹妹,滚,滚回你们五号船去。我这么大发雷霆,孙喜明他们知趣了,纷纷离开我家舷板,我们是该走,都走吧,舱里还有个小可怜呢,让她好好睡一会儿。樱桃的母亲也带着儿女走了,但是她对我的态度有意见,嘴上一定要报仇,临走丢下一句阴阳怪气的话,这父子俩,把人家小女孩子藏在舱里,还要撵人走,准备干什么啊?樱桃母亲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我都不知道如何还击了,德盛女人在一边听不下去,高声道,樱桃她妈,你说这种话要小心中风啊,明天落个歪嘴病可怎么办?
一场风波连着一场风波,七号船总算静下来了。一个神秘的礼物在寂静中向我打开,我家船舱里的沙发像船中之船,载着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往下游去。船队已过养鸭场,河面变宽了,来往的船只少了,船尾的浪声反衬着船上死一般的寂静,后舱里的小女孩在睡梦中忽然惊叫了一声,妈妈,妈妈在哪里?那响亮的梦呓把我和父亲都吓了一跳,幸好她是在梦里,她在沙发上焦躁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我注意到她的一只袜子脱落了,小脚丫子正对着我,微微晃动着,闪着一圈模糊的白光。
我和父亲守在舱门口,像两个警卫员守护着一个沉睡的小女孩。父亲沉默着,看上去满腹心事,我不知道他是沉浸在自己的羞耻中,还是在为沙发上的小女孩犯愁。每逢这样的场合,我先说话是不利的,说什么都错,我等着父亲先说。果然,父亲自己打破了沉默,他问我,这孩子的妈妈死了吗?我说,多半是死了,投河自杀了吧。父亲沉吟了一会儿,说,自杀就是逃避呀,她自己倒是解脱了,这小女孩以后要受苦了。
船过鹿桥村,德盛夫妇来了,来打探孩子的动静。不知为什么,那夫妇俩看上去一个喜不自禁,另一个鬼鬼祟祟。德盛女人问我,那孩子乖不乖?我说,还没醒呢,睡得那么死,我怎么知道她乖不乖?德盛看看我,又看看我父亲,脸上突然露出一种诡谲的神情,他推了推女人,你不是有话要跟库书记说吗?趁着现在没闲人,快说呀!德盛女人瞪了男人一眼,说,我开玩笑的话,你倒当真了,我说了库书记肯定要见笑的。我父亲不解其意,看着德盛夫妇,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船挨船的,是邻居,千万别见外。德盛女人扭捏起来,指着舱里掩嘴一笑,也没什么,我看着这小女孩,不知怎么就想起我自己来了,我小时候也是让爹妈扔在码头上,我婆婆把我捡到船上养起来的,养大了就让我嫁了德盛,谁不说我婆婆精明?积了德行了善,还顺便攒下个儿媳妇。德盛在一边催促女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绕什么圈子?德盛女人打了德盛一下,不绕圈子,道理说不清!她对我父亲说,库书记你别嫌我多嘴,我看这孩子跟你们七号船是有缘分的,看看你们老少三个,其实都是一个命,库书记,你的革命妈妈不是牺牲的吗,东亮虽然有妈妈,可惜跑啦,这小可怜的妈妈呢,干脆投水自尽啦,都是可怜人,你们三个有缘分呀!德盛听得不耐烦,瞪着他女人说,天都黑了,你还绕圈子?有缘分怎么的,你倒是快说呀。德盛女人被催得乱了方寸,终于说了,库书记你别嫌我多嘴,你们船上没女人呀,没女人不行,要是把这小女孩留在船上,以后长大了就攒下——德盛女人没有说下去,因为我父亲慌张地打断了她的话,不行不行,我们不养童养媳。父亲不停地朝德盛夫妇摆手,苦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是好意,可是你们不懂规章制度啊,捡一个孩子不是捡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很麻烦的,要登记要调查,谁家也不能随便留的,别说这孩子这么小,就是个现成的小媳妇大姑娘,也不能留!
我被德盛女人弄了个大红脸,不知她怎么想出来这个锦囊妙计。德盛女人对德盛翻着白眼,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过库书记不会同意的,你非要自讨没趣!说着她瞥了我一眼,表示遗憾,你们男人不会看女孩子呀,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会出落成个大美人的。她叹了口气,又朝后舱探出脑袋,集中精力去听女孩甜蜜的呼声,听了一会儿她大发感慨,说,这孩子命很旺的,没有爹妈照样活,你们听,她打呼打得多响,跟一头小猪似的。
德盛夫妇给小女孩留下几个玉米,怏怏地走了。河上的天空突然一暗,夜色慢慢垂下来,覆盖了漫天的雨云,岸变黑了,我家的后舱也黑了。小女孩还在睡。我和父亲之间,突然被一种很古怪的气氛包围了,我父亲想解释什么,不知从何说起,而我想表白什么,却羞于做任何表白。父亲把油灯挂在舱房的梁上,拧了一小簇火苗,舱房里亮了一圈,我看见了父亲脸上焦灼不安的神情,他弯腰俯视着后舱里的小女孩,突然说,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要防微杜渐!
我疑惑地看着父亲,你说什么,什么防微杜渐?
父亲说,天黑了,要过夜了,这小女孩,不能在我们船上。
我猜到了父亲的心思,一下打了个寒颤。父亲的脸在油灯的光线里显得深谋远虑,你瞪着我干什么?他注意到我不满的表情了,挥挥手说,有些事情你不懂的,这么小的女孩,也是女的!是女的就不能在我们船上过夜,我们得把她送走!
把她送哪儿去?我问父亲。
送给组织。父亲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醒悟到向阳船队是没有什么组织,便说,送到孙喜明船上去,他是队长嘛。
我知道凡事牵扯到男女关系,都是大问题,必须听父亲的安排。我下到舱里,替慧仙把袜子穿好,拍着她的脚说,醒醒,我们走。小女孩醒了,踢了我一脚,咕哝道,别烦我,我要睡。她的脑袋侧过去,还要睡。我说,不能睡了,天黑了,我们家有老虎,夜里出来咬你。她一骨碌坐起来,瞪着我,骗人?老虎在哪里?你骗人的。她还要往沙发上躺,我像是扛箱子似的,反扣住她柔软的小小的身体,一下把她扛到后背上去了。我感觉到她在我背上挣扎了几下,平静下来了,一觉醒来她又想起妈妈,对我命令道,那你快点,你背我去找妈妈。我说,你不懂事,你妈妈躲着你呢,我不知道你妈妈躲哪儿去了,领导知道,我把你交给领导,让组织上替你找妈妈去。
夜色中我背着慧仙往孙喜明家的船上去。驳船上的桅灯都亮了,我背着慧仙走过了六条船,六条船上的人都拦住我,问我要把小女孩背到哪里去。我说,天黑了,我把她交给孙喜明去。王六指的几个女儿试图拦截慧仙,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说她可爱,央求我把慧仙留在他们船上,她们要陪慧仙过夜。我说,不行,你们船比鸟窝还吵,你们这些黄毛丫头也不算个组织,我要把她交给孙喜明去。
一号船上的孙家人刚刚吃了晚饭,孙喜明女人在暗淡的桅灯下刷刷地洗着碗筷,看见我背着女孩上了她家的船,惊叫起来,你怎么把她背来了?黑咕隆咚地走这么多船,多危险!她喜欢睡你家的沙发,就让她睡嘛。你别小器,那么好的沙发,睡不坏的。
不是我不让她睡沙发,是我爹不让。我一时不知怎么解释,就把父亲的话抬出来了,我爹说了,她是女的,不能在我们船上过夜!
孙喜明女人笑起来,笑得弯下腰,这库书记也是的,什么女的女的,这孩子多大一点呀?樱桃她妈乱嚼舌头的话,他也往心里去了?我看你爹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小心,再提防,也不至于这个孬样呀。
我笑不出来,气呼呼地把慧仙往她怀里塞。孙喜明一家人都围过来了,看起来他们是乐意接收慧仙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话,研究着慧仙的辫子和衣服,孙喜明撵走了儿女,对我说,送过来也好,你们船上没个婆娘,也伺候不了这孩子。
慧仙从我的背上下来时,含糊地哭了几声,她仍然睡眼朦胧。孙喜明女人用力把她抱了起来,慧仙犟着,小脸上有明显的嫌弃之色,是女人耳朵上的一对金耳环吸引了她,她瞪着女人的耳朵,先抓了左耳,又去抓右耳,孙喜明女人欢喜地握住了她的小手,对她说,喜欢我的金耳环呀?长大给我做儿媳妇,两个金耳环,都归你!
是我把慧仙背到一号船上去了。我记得我从孙喜明家往回走,光脚走过六条船冰凉的舷板,越走脚下越凉,一条船凉过一条船。乌云被夜色覆盖了,雨没有落下来,金雀河的尽头早早地升起半个月亮。河上夜色初降,两岸蛙鸣喧天。夜航的船队在河上突突地前进,河水在我脚下汹涌奔流。我的脖子那儿有异样的感觉,一摸,是小女孩辫子上的牛皮筋粘在我脖子上了。我记得很清楚,走过王六指家的舷板时,我还把牛皮筋搭成一把弓箭,朝王六指的小女儿射了过去。我不高兴,也没有什么不高兴。我很正常。反常的是我的后背,一去一回,我的背上已经空空荡荡,一个小女孩带给我的温暖的体温荡然无存,我的后背竟然还保持着惯性,微微弓起来,承接一个不存在的小小的柔软的身体。我的后背有点卑贱,卑贱得很反常,分别不到两分钟,我的后背就开始思念起一个小女孩了。
我弓着背走到我家的船上,看见一盏孤灯在舱棚里摇晃,父亲已经在舱下整理床铺。船上一片凄清,似乎没有人烟,那是第一次,我打量着舷板上一条薄薄的哀伤的影子,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孤独,还有爱意,它比夜色中的河水更加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