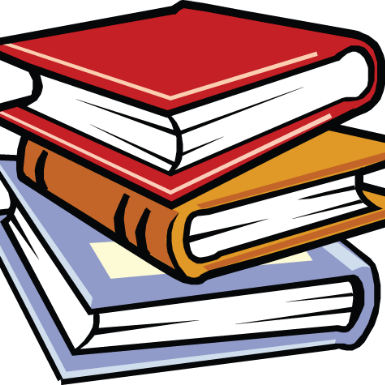牛月清第二天上街买了被面和一套咖啡壶具,晚上回双仁府那边老太太处睡,翻寻存放在那儿的一只电熨斗。电熨斗是庄之蝶一次去一家工厂讲课时赠得的,一直没用,牛月清想一并送了礼。但老太大知道了这事,说要送尿盆的,尿盆最重要,老一辈人谁结婚娘家不陪送了尿盆的;现在人是少了规矩,娘家人不陪,亲戚朋友也不送。牛月清就想,真是送个搪瓷痰盂做尿盆,那岂不出奇制胜?人也常说,谁和谁能尿到一个壶的,这尿盆上辈人为啥讲究,怕也取其夫妻百年合好的意思吧。但她知道现在痰盂在商场里没货的,前几日单位有人跑了全市商场没买到,后来还是在西城门内的鬼市上买的。于是隔了一天的清早,就去了鬼市,问了几个摊主,说货没有了,你去洪江收购店看有没有?牛月清听了,倒生疑惑,怎么有个洪江收购店?世上有人名叫洪江的,店名也有叫洪江的?就问:这店名好怪,怎么起这个字号儿?那人说:哪里是字号,是叫洪江的开的店,人叫顺了,就这么叫开来的。牛月清问:那个洪江,是干什么的?那人说:开了个书店吧,听说发财了,又来开收购店,更是发海了!你是查户口的吗?牛月清赶忙走了,再问了别人洪江店在哪儿开的,有人指点了,果然在前边一条巷中间。店门是开了,里边有一个老头在坐着。牛月清上去问:这是洪江收购店吗?老头说。以前是,现在不是。牛月清说:那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怎么回事,饥不择食,穷不择妻,温饱了思淫。人家有钱了,看上鲜的嫩的了就离起婚。他老婆哪里肯离,他就给了五万元,又送了这个店。现在兴掏钱离婚的。牛月清脑子里就乱哄哄起来,赶忙回家对庄之蝶说了。庄之蝶道:他能一直瞒了咱们,必是离婚时有纠缠的。牛月清说:我不是这意思。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事吗?以前他穷成那样。
从没听说过他还有个收购店,怎么能办起个收购店?这一离婚,给了原先老婆这个店,还有五万元,他这是哪儿的钱?庄之蝶说:你不是一月十天地就要过目一次帐面吗?牛月清说:别人办书店都发了,咱不是亏就是平平。我是疑心过,可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有经验,你又过问过几次?!庄之蝶说:这没证据,你怎么说他?牛月清说:那就咱养猪他吃肉了!?庄之蝶说:我还有画廊的。画廊和书店合为一体,生意就好了。牛月清叫道:你是让赵京五出来监管了他?庄之蝶说:你不是又要一心把柳月嫁给你干表姐的儿子吗?牛月清突然眉开眼笑起来:哎呀,你还这么鬼的!你是早就看出毛病来了!庄之蝶说:你以为你行哩?!说得牛月清一睑羞愧。
二十八日,牛月清代表庄之蝶去参加洪江婚礼,礼品十分丰盛,洪江夫妇好不高兴,特将礼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宴席上第一个给牛月清敬酒,又当着众人面高声说,庄老师今日有紧急会议不能抽身,师母既然是双重身分,就要替庄老师再受敬一杯。牛月清便喝得面红耳热。庄之蝶却并未去开什么会议,找了赵京五催促画廊筹建的事,得知画廊基本上装修完毕,只是字画作品少,一时还不能开张。庄之蝶提出去看看那些仿制名人字画的人,赵京五说:你还是不去为好,实话给你说了,这批活还是汪希眠在干哩,他让我谁也不告诉,包括你在内,怕的是有个疏忽说溜了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事情就坏了。庄之蝶听了,说:你不说,我十有六七也猜出是他!西京城里的画家我差不多认识,能仿制膺品的除了他,也再没一个两个。前一阵听说广州香港那边石鲁的假画很多,石鲁的家属到处查访,已经风言风语说到了他,他也不缩缩手脚?赴京五说:这我知道,石鲁那批假画原本是给咱们画廊的,说好画廊售出咱拿四成,他得六成。可旅行社的一个余导游却不知怎么和他谈的,竟把那批画全拿了去广州出手。这些假名人字画靠国内市场是不行的。主要是骗海外人。外宾来了,他们哪儿知道在哪儿卖字画。全凭导游引团。为这次教训。我已去旅行社新交了几个哥儿们了,答应咱的画廊开张,就领外宾来买画,咱又给他们吃些回扣罢了。汪希眠现在手下有三个学生,专协助了他为咱画廊仿,一批古画,譬如郑板桥的风竹呀,齐白石的虾呀,黄宾虹的山水呀。石鲁的画不敢多弄的,但石鲁的画眼下抢手,少也要弄出个二三幅的。前几日我去看了,汪希眠已仿制了石鲁早期的一张《牧牛图》,还有一幅石鲁病后的《梅石图》。真了不起的,昨儿夜里我拿了《梅石图》去让石鲁的女儿看,她也没看出假来,还问哪儿得来的?我说是从一个小酒馆的师傅那儿买的,她说:我爹病了以后,常常这些人让他去喝酒;喝了酒,老爷子没钱,提笔就给人家画一张的。赵京五说完,哈哈大笑。庄之蝶也笑着说:汪希眠不让我知道,可他哪里却知道这画廊是我在办的?!其实他那老婆与你师母亲得如姐妹,汪希眠于什么事她不给我说?就掏出旱烟斗儿来装了烟吸。
赵京五瞧见烟斗,说:哪儿得的,这烟斗年代不新,还是个古董货哩!庄之蝶笑而不答,只说龚靖元的那幅毛泽东的字怎么样?还是不行吗?赵京五说:我正要对你说这宗事的。等那件作品弄到手了,咱画廊就可以开张,到时候开个新闻发布会。画廊不愁生意不好的。龚小乙那边,我已治住了。庄之蝶说:怎么个治住了?赵京五说:他是烟瘾不发,什么都精明能算计;烟瘾发了,你让他叫爷也十声人声叫的。上次我对他说我能让柳叶子压了价供他的大烟,当然了,我就也可以让柳叶子提了价供他大烟,或者金山银山的拿来都不供他大烟的!我已经给柳叶子说了,不管怎样,十天里不能供给他一包烟的,除非他把那幅字拿来。庄之蝶说:这柳叶子是什么人?和贩烟土的人打交道你可要小心,这是要犯法的。赵京五说:这我知道。我一不吸,二不参与分钱。柳叶子是我小学的同学,她和她丈夫干了几年贩烟的黑道儿了,龚小乙也只有她这一个买烟土的渠道。庄之蝶说:做那黑道生意的唯钱是命。她哪里就肯听了你的去逼龚小乙?赵京五说: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去年她把一批烟壳子卖给东羊市街一家姓马的,姓马的开的重庆火锅饭店,汤里就放着烟壳,顾客盈门,都说马家火锅香,已馋得许多人每日都去吃一次,不吃心就发慌。有人怀疑那汤里有烟壳儿,暗中观察,果然有,就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封了火锅店,追问烟壳哪里来的?
姓马的供出了柳叶子,柳叶子在派出所谎说是前年她爹患胃癌,乡里医生给开了一包烟壳让熬汤喝,她爹去世了,烟壳没用完,她觉得丢了可惜.卖给姓马的。派出所怎么能相信?那所长是我一个哥儿们,我便去说情,事情就按柳叶子说的那样作了结论,把她才放回来。你想想,柳叶子哪里能不听我的?你今日没事,咱去柳叶子家去看看,兴许那幅字已经放在她那儿了。两人搭了出租车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庄之蝶却不想去了,说他还是不认识柳叶子为好。赵京五想了想,就让他去巷口小酒店等着,自个去了。没想柳叶子夫妇都在,一见他就悄声说:龚小己正在楼上过瘾哩,他今日把那字拿来了,怕我还是不供烟,说过了瘾,又能买到一批烟了才一手拿烟一手给字的。你不要惊动他,到小房喝茶吧。赵京五却不放心,蹑手蹑脚从楼梯上到二楼,隔门缝往里看了,龚小乙是睡在床上,人已瘦得如柴。身边真的放着那卷字轴儿。便笑着下来喝茶去了。
龚小乙在家烟瘾发了几天,一日三趟往柳叶子这儿跑;柳叶子就是不供烟,须要了那幅字不可。龚小乙就强忍着难受返回。回去了又立坐不宁再跑来求;求了不行,再回去;又再来又再回去,如此五次。他觉得浑身疼痛起来,拿头在墙上撞。把胳膊在床板上摔。一撮一撮往下打头发,末了只得拿了那幅字来到柳叶子家,一扑进门就倒在地上,满口白沫要给柳叶子可磕头。柳叶子见他拿了那幅字,展开看了,见是毛泽东的书法,龙飞凤舞,气象万千,大有个代领袖人物的气派,倒心想赵京五怪不得这么垂涎三尺,一心要得到这字的!就卖给了龚小乙烟土,龚小乙得了宝贝。便上楼先去解并瘾,说死抱了字幅不放,要过了瘾后再卖给他一批烟了才交字幅的。
龚小乙上了二楼,急急吸了烟,放平在了床上。想着这么多天那个狼狈样也着实有些后悔。当初自己是爹的宝贝儿子,一表人材,聪明伶俐,常跟了爹出去,谁个不夸爹的字好爹的儿好。有多少人提出要和爹作儿女亲家,有多少漂亮的女子一见到自己就那么媚笑,他那时是谁也不看在眼里的。可如今要工作没工作,爹嫌弃,亲戚朋友贱看,连塌鼻子的柳叶子也勒克他。就在他刚才来时,柳叶子正和她男人在屋里干事,看见他了,竟也不避。他是鼻涕诞水地跪地乞求,她倒一边提了裤子,一边把一条巾布从腿中掏出来和他说话,她全然是把他不当了人了嘛!龚小乙愤慨在没烟的时候世界对他是如此刻薄狠毒,他只有在吸了烟后的麻醉中去觅寻自己的幸福,去报复这个世界了。这么想着,眼前果然就出现一片灿烂,龚小乙又是过去的龚小乙了,年轻英俊,神气勃勃。他便有了一个绝妙的念头:让墙上那挂钟的时针和分针突然停止,让时间突然停止,让他生出翅膀巡看这个城市的每一户人家在同一个时候里都在干什么?果然,挂钟的时针和分针都咔地一声停住了,那一直在房子里飞来飞去的一只苍蝇也停止在空中。他就有翅膀从胳膊下生出,开始从城墙西门口一家一家往过看,直到东门口。又从北门口一家一家往南看到南门口。他看清了,在这同一瞬间里,几乎所有人家的床上,都赤裸裸地有男女在交媾,动作千姿百态。龚小己就走进去。他收拾那些肮脏的精液,竟汇集了三个大洗澡盆;洗澡盆也盛不了,他装在水车里,就是每日清晨街上的洒水车。然后从井字形的大街上一路走一路喷洒。他闻见了一段极浓的腥臭味,他说:我把你们的孩子都消灭了!再后来,龚小乙集中了所有男人,割掉了他们的生殖器;割下一条就扔进城河里,城河里差不多要填满了,推倒了城墙把它们理掉。他还要当了这些男人们的面开始奸污所有的女人,他让她们大声叫喊,让她们的男人们难受嚎哭。他要这样,要这样才觉得开心。最后他就穿上了一双巨大的草鞋,在广袤的八百里秦川上奔跑,奔跑过了那一座一座足以令西京人骄傲的如山丘一样的帝王坟莹,看见了乾陵。父亲曾经说过,乾陵是武则天特意建造了一个女人仰躺在平原上的形状。现在,那不是坟墓,分明是美丽高贵的武则天活活地仰面躺在那里,他就过去将她强xx了!是的,他强xx了她,满天风起云彩飞扬,回过头来则发现平原上那一个个山丘般的帝王陵墓都平陷下去,方明白那陵墓中的帝王死了而生殖器没死,没死还长着,所以陵墓才这么高的;而此时看着他占有了一切,征服了武则天,就全蔫下去了,绝望而死了!龚小乙是多么痛快,他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市长,这个城市的市民都是没有了交媾能力的男人和被他占有的女人,所有的钱都是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是他的,所有的大烟都是他的……赵京五在楼下的小房里喝过了三壶浓茶,龚小乙迟迟不能下来。柳叶子陪着他嗑瓜子儿说话,她那丈夫却在院门口喊:喂,疯老头子,收不收废纸?我家厕所有一堆用过的手纸,你去拿了,不收你钱的!便听见一个苍哑的声音念唱道:腰里别的bb机。手里拿的步话机。馆子里吃烧鸡。宾馆里打野鸡。
柳叶子的丈夫就嗬嗬地笑,说:说得好,说得好!柳叶子骂道:胖子,你又和那收破烂的老头拌什么嘴儿?那丈夫却不理,还在门口朝外说:你还收旧女人不收?如果你收旧女人了,我敢说这个街上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把老婆去旧换了新的!柳叶子就扑出去,拧了丈夫的耳朵往回扯,骂道:你还要换老婆?能换的话我第一个先换了你这癞猪!赵京五没有过去拦挡,只悠悠地听门外远处的吆喝声:破烂--!承包破烂--喽!主人家吵吵闹闹了一阵,柳叶子进来了,说:小乙还没下来?赵京五说:你去看看。柳叶子就站在院子里朝楼上喊:小乙,小乙,你该受活够了吧?!龚小乙从幻境中惊醒,从楼上下来,走下来还未彻底摆脱那另一个世界里的英雄气概。说道:吵吵什么,你是欠操吗?柳叶子骂道:你说什么?一个巴掌扇过去,龚小乙清醒了。那一个巴掌实在太重,小乙麻秆一样的腿没有站稳,跌坐在台阶上,柳叶子伸手去夺了字轴儿。龚小己说:柳叶子姐姐,咱说好的,不卖给我十二包,这字你不能拿的!柳叶子笑了,交给他了小小的十二个纸包儿,收了一卷钱。龚小己说:庄之蝶和我家世交,他要拿东西交换这字,我也没给的,这我可等于白白给你了,柳叶子姐姐!柳叶子说:你走吧,你走吧!推出去,就把院门关了。
庄之蝶得到了毛泽东手书的《长恨歌》长卷,便去找各家报社、电视台及书画界文学界的一帮朋友熟人,说是他和旁人要合办一个画廊而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希望能给予支持。众人先以为仅仅是个画廊,虽然庄之蝶开办画廊是件新鲜事,但要在报纸上电视上作大量宣传就有些为难了,因为画廊书店一类的事情社会上太多,没有理由单为他的画廊大张旗鼓。庄之蝶自然提出他有一幅毛泽东的书法真迹。众人就说这便好了,有新闻价值。于是来看看,叹为观止,有的便已拟好文稿,只等新闻发布会召开,就立即见报。因为是私人召开新闻发布会,预算了招待的费用不少,牛月清就召了赵京五和洪江筹备资金。洪江拿了帐本,七算八算只能拿出所存的三千元积存,叫苦书店难经营的。牛月清就说正因为难经营才开办这个画廊的,现在咱们画廊书店合一,以后经营主要就靠画廊了,要洪江给赵京五作好帮手。洪江明白,以后这里一切将不会由自己再作主了,心里不悦,却没有理由说得出口,也就说:京五比我神通广大,那太好了,以后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跑。我是坐不住的人,跑腿儿作先锋可以,坐阵当帅没材料的。牛月清说:京五,洪江这么佩服你,你也得处处尊重洪江意见,有事多商量着。三人出门走时,故意让赵京五先出去了,把一节布塞在洪江怀里,悄声说:这是我托人从上海买来的新产品,让晓卡做一件西式上装吧。装好,别让京五看见了,反而要生分了他。因为画廊的事,庄之蝶已是许多天日没去见唐宛儿,这妇人在家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一段日子来,她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饮食大减,眼皮发胀,动不动就有一股酸水泛上来,心里就疑惑,去医院里果然诊断是怀了孕了。先是从潼关到西京后,周敏嫌没个安稳的家,是坚决了不要孩子的,每次房事都用避孕套的,所以一直安全无事。自和庄之蝶来往,两人都觉得那塑料套儿碍事,于是都是她吃些避孕药片,但总不能常把药片带在身上,偶然的机会在一起了,贪图欢愉,哪里还顾了许多,庆幸数次没有怀上,越发大了胆儿,以后便不再吃药。如今身子有了反应,吓得妇人怕露了马脚,只等周敏上班去了。就一口一口在家里吐酸水儿,吐得满地都是。急着把这事要告诉庄之蝶,盼这个男人给自己拿个主意,壮壮胆儿;也可将自己的苦楚让他知道。但白鸽子捎去两次字条儿,庄之蝶却并没有来。妇人的心事就多起来,估摸是庄之煤故意不来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事儿缠身?又不敢贸然去他家走动,不免哭了几场,有些心寒。却又想,这孩子无论如何是出不得世的,即使庄之煤一心还爱了她,等着他来了,也还是要去医院堕胎的;又不知几时能来,何必自己多受这份惊怕和折磨,不自个去处理了呢?有了这个主意,倒觉得自己很勇敢的。能怀了孩子就可以为庄之蝶证明他是行的,又不娇娇滴滴地给他添麻烦,庄之蝶越发会拿她和牛月清相比,更喜欢了她的!于是这一日早晨,周敏一走,妇人独自去了医院堕胎。血肉模糊地流了一摊,旁边等候也做流产的一个女子先吓得哭起来,唐宛地倒十分地瞧不起,待医生说:你丈夫呢,他怎么不来陪护了你?她说了声:在外边哩,他叫的小车在外边等哩!走出病房,一时有些凄惨。在休息室坐了一会儿,心静下来,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兀自笑了一下,自语:我唐宛儿能吃得下砖头,也就能屙出个瓦片!起身往家走。走过了孟云房家住那条巷,身子并不感到难受,只是口渴,就想去孟家喝口水儿,也好打问打问庄之蝶的行踪。一踏进门,孟云房并不在,夏捷正噘了嘴在屋里生闷气儿,见了唐宛儿便说:才要去拉你到哪儿散了心的,你却来了,真是个狐狸精儿!唐宛儿说:是狐狸精的,你这边一放骚臭屁儿,我就能闻着了呢!嘴噘得那么高,是生谁的气了?夏捷说:还能生谁的气?唐宛儿说:又嫌孟老师去在老师那儿闲聊了?!这么大的人,还像个没见过男人似的,一时一刻要挂在裤带上吗?夏捷说:庄之蝶这些天忙活他的画廊,人家哪有闲空儿和他聊?要是光聊天倒也罢了,一个新疆来的三脚野猫角色,他倒当神敬着,三天两头请来吃喝,竟把孟烬也招来拜师父……我才一顿骂着轰出去了!甭说他了,这一说我气儿又不打一处来!宛儿你怎么啦,脸色寡白寡白的?唐宛儿听她说庄之蝶这些天是忙活着画廊的事,心里倒宽松下来,就说:我睑是不好吗?这几日晚上总睡不好的,刚才来时又走得急了,只害口渴。有红糖吗?给我冲一杯糖水来喝!夏捷起身倒了水,说:晚上睡不好?你和周敏一夜少张狂几回嘛!热天里倒喝红糖水儿!唐宛儿说:我这胃寒,医生说多喝红糖水看好。喝罢了一杯,唐宛儿浑身出了些汗,更是觉得有了许多精神头儿,说了一会话,夏捷就提议去街上溜达。唐宛儿原本喝了水要回去睡一觉的,却又被夏捷强扭着,也就走出来。
两人说说笑笑走出城南门口,唐宛儿便觉得下身隐隐有些疼,就倚了那城河桥头上,说:夏姐,咱歇会儿吧。拿眼往城河沿的公园里看。天高云淡,阳光灿烂,桥下的城河里水流活活,那水草边就浮着一团一团粘糊糊的青蛙卵,有的已经孵化了,鼓涌着无数的小尾巴蝌蚪。唐宛儿不觉就笑了。夏捷问笑什么,唐宛儿不愿说那蝌蚪,却说:你瞧那股风!一股风是从河面上起身,爬上岸去,就在公园铁栅栏里的一棵树下张狂,不肯走,不停地打旋儿。原本是不经意儿说着风,风打旋的那棵树却使两人都感兴趣了。这是一棵紫穗槐的。粗粗的树干上分着两股,在分开的地方却嵌夹着一块长条石,十分地有意思。夏捷说:这树的两股原是分得并不开吧,园艺工拿块石头夹在那儿。树越长赵大,石头就嵌在里边了?唐宛儿说:你看这树像个什么?夏捷说:像个丫字。唐宛儿说:你再看看。夏捷说:那就是倒立着的人字。唐宛儿又说:是个什么人?夏捷说:人字就是人字,还能看出个什么人来?唐宛儿说:你瞧瞧那个石头嘛。夏捷就恍然大悟,骂道:你这个小骚×,竟能想到那儿去!就过来要拧唐宛儿。两个人嘻嘻哈哈在桥头栏杆上挽扭一堆,惹得过往路人都往这边看,夏捷说:咱别闹了,人都朝这儿看哩!唐宛儿说;管他哩,看也白看!夏捷就低声说:宛儿,你老实给说,周敏一天能爱你几次?你是害男人的人精,你没瞧瞧周敏都瘦得像是药渣了!唐宛儿说:这你倒冤了我,我们一月二十天地不到一块儿,那样的事差不多就常忘了哩。夏捷说:那你哄鬼去!甭说周敏爱你,我敢说哪个男人见了你都要走不动的!唐宛儿笑说:那我真成了狐狸精了?夏捷说:说狐狸精我倒想起昨夜的事了。昨儿夜里我在家读《聊斋志异》,满书写的孤呀鬼呀的,就害怕了。你孟老师说:狐狸精我不怕的,三更半夜了我就盼有个狐狸精吱地推了窗进来。我就骂他你想得美,凭你那一身臭肉虼蚤都不来咬你的!睡下了也想,蒲松龄是胡写哩,世上哪儿就有狐狸成精,要说人见人爱的女人,我这辇子也就见着你这一人了!唐宛儿听了,便说:我读《聊斋志异》,却总感觉蒲松龄是个情种,他一生中必是有许多个情人。他爱他的情人,又苦于不能长长久久做夫妻,才害天大的相思把情人假托于狐狸变的。夏捷说:你怎么有这体会?是你又爱上了什么人,还是什么人又在爱你了?唐宛儿脑子里就全是庄之蝶了,她把眼睛勾得弯弯的如月牙儿,脸上浮一层笑,蓦地腮边飞红,却说:我只是瞎猜想,哪儿就有了情人?夏姐儿。这世上的事好怪的。怎么有男人就有了女人……你和孟老师在一块儿感觉怎样?夏捷说:事后都后悔的,觉得没甚意思,可三天五天了,却又想……唐宛儿说:那你们可以当领导!夏捷说:当领导?唐宛儿说;现在机关单位当领导的,哪一个不常犯错误?犯了错误给上边作个检讨,检讨过了,又犯同样的错误。就这么犯了错误作检讨,检讨了又犯错误,这官就继续当了下去!说罢两人又笑个不止。夏捷说:人就是这饮食男女嘛!唐宛儿说:其实人就是受上帝捉弄哩,你就是知道了也没个办法。夏捷说:这话咋讲的?唐宛儿说:我常常想,上帝太会愚弄人了。它要让人活下去,活下去就得吃饭;吃饭是多受罪的事,你得耕种粮食,有了粮食得磨,得做,吃的时候要嚼要咽要消化要屙尿,这是多繁重的事!可它给人生出一种食欲,这食欲让你自觉自愿去干这一切了。就拿男女在一块的事说,它原本的目的是让遗传后代。但没有生出个性欲给你,谁去干那辛苦的工作呢?而就在你欢娱受活的时候,你就得去完成生孩子的任务了!如果人能将计就计,既能欢娱了又不为它服务那就好了!夏捷说:你这鬼脑子整日想些什么呀?!拿手就来搔唐宛儿的胳肢窝。唐宛儿笑险得不行,挣脱了跑过桥头,夏捷偏要来追,两人一前一后跑进公园的铁栅栏门去,唐宛儿就趴在那一片青草地了。夏捷一下子扑过去按住,唐宛儿没有动。夏捷便提她的腿,竟把一只鞋脱下来,说:看你还跑不跑?!唐宛儿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夏姐!嘴唇惨白,满脸汗水,眼睛翻着白地昏过去了。
当夏捷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唐宛儿送往医院的路上,唐宛儿醒过来了,却坚决不去医院。
说她早年患有昏厥病的,这几天劳累怕是又犯了,回家歇一歇就没事儿的。夏捷用手摸摸她的额。额上汗已不凉,也见睑色有些红润,便不再往医院送,多付了五元钱给车夫,就一直把唐宛儿送回家来。屋里冷冷清清的,唐宛儿进门先上床躺了。夏捷说:宛儿你现在感觉好些吗?唐宛儿说:好得多了,多谢了夏姐。夏捷说:你今日给我收了魂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真是不活了!唐宛儿说:那咱姐妹儿就去做风流鬼吧!夏捷说:这阵子你还说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的?唐宛儿软软地笑,说:什么也不想吃的,只想睡觉,睡一觉起来什么都好了,你回去吧!夏捷说:这周敏也不在家了,他是上班去了?我去给他单位拨个电话吧!唐宛儿说:你回去的路上给地拨个电话吧,你先给庄老师家拨,可能周敏在他那儿的。夏捷就又给冲了一杯红糖水放在床边,拉上门就去街上拨电话了。
电活拨通了庄之蝶,庄之蝶得知唐宛儿突然病了,骑了木兰急急就赶过来。周敏还没有从杂志社回来。唐宛儿一见面呜呜地哭起来。庄之蝶一边替她擦了眼泪,一边问病情,待妇人说了原委,只惊得跌坐了床沿上半天不起来,然后就拿了拳头砸自己脑门。唐宛儿见他这样,心里自是高兴,却说:你是恨我吗?我对不起你,我把你的孩子糟踏了!庄之蝶一下子抱了她的头,轻声说:宛儿,不是你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这种罪过应该让我受,你却一个人独自去承担了,你真是个好女人!可你才作了手术,却怎么不爱惜身子,倒要陪夏捷去劳累?!唐宛儿说:我感觉我能行的,再说我能让夏捷知道这事吗?画廊的事怎么样?庄之蝶说:你怎么知道我忙画廊的事?我好久不得过来,你却也不让鸽子捎了信去。唐宛儿说:我哪里没捎信去?整日整夜盼了你来,一直没个踪影了,我才自做了主张。庄之蝶骂了一句柳月,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的,就揭了被子看那伤处,然后就重新掖好,出门去街上买了一大堆营养滋补品,一直陪着等到周敏回来才回去。
自此一星期里,庄之蝶隔一天去看望唐宛儿一次。少不得要买些鸡和鱼的。柳月每次待他回来,就沏一杯桂圆精饮料给他,他说:柳月会体贴人了?!柳月说:给你当保姆还能眼里没水?你又出了力了嘛!庄之蝶就笑着说:我现在不敢出门了,一出门你就认为到唐宛儿那里去了!我哪里也不去了,你去替我办事吧,找着赵京五,让他请了宏大夫到清虚庵去。柳月说:清虚庵的慧明病了?上礼拜天我在炭市街市场买鱼,回来就看见慧明了。
她和黄秘书坐的一辆小车停在路边,她没看见我,我也装着没看见她。哼,做了尼姑也是要涂口红吗?我就瞧不起她那个样儿,要美就不要去当尼姑,当了尼姑却认识这个结识那个的,我看她是故意显夸自己。不当尼姑,满城的漂亮女子谁知道几个名儿姓儿的;做了尼姑,人人却知道城里有个慧明的白脸大xx子尼姑!她怎么病了,佛也不保佑了她?庄之蝶说:瞧瞧.担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人家漂亮了你气不过!柳月说:我气过谁了?庄之蝶才要提说唐宛儿让鸽子捎信的,话到口边却咽了,他在家并未对牛月清和柳月提说过唐宛儿病了的事。柳月却还气不顺地,说:与我的屁事!以前孟臭嘴往那儿跑了,现在眼瞎了不跑了,你就跑得勤快!庄之蝶说:你越说越得意了!我也是在路上见着黄秘书,他告诉说慧明腰疼得直不起来,我才让赵京五去请来大夫的,你要不去就算了。柳月说:你说了话我能不去?今日午饭我回来迟了,你和大姐去街上吃吧。庄之蝶说:说句话能用多少时间?你要把魂丢了,回来我告知你大姐的!。柳月说:好么,那我就让大姐撤一把毒谷子把白鸽子毒死去!说罢就笑着出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