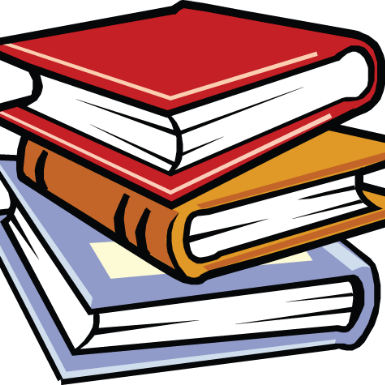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致维熙
维熙兄:
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只能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我也不想介入这种辩论,因为这实质上可归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同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永恒规律的无休无止的探讨。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文学家应该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个命题可以成立。而现在,我们文学家面对这样迅猛发展的时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认为我们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要表现社会、表现时代、表现历史,没有对社会、时代、历史的较全面较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些文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谈起文学来或许能头头是道,但是对文学以外的领域毕竟是生疏的。这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环境中,也许还能应付,还能写出一些不错的作品,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人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单个人具有的狭隘的知识,就表现了“原始的丰富”。而今天,“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形成了一幅广阔而多变的社会图景,并且把我们的昨天和传统习惯等等也要放到新的历史天平上来衡量;人的能力(体力的和智慧的)已接触到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变革,新的理论、观念、艺术见解、技术进展与新的经济和社会的创见,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地涌现,造成了人的新的智能环境,于是人扩展了自己;工业社会的集中化、标准化、同步化、专业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并不会消除人的个性,相反,我们的人民正是借助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物质条件充分地展开各自的个性。总之,文学是写人与社会的,在我们面前的人与社会已开始了巨大的发展,我们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家如不随之发展,不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就等于自行取消写作当代题材文学作品的资格。同时,作家的勇气不但来自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感,还要来自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与自身知识的全面性。
其次,我认为我们现在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必须“创造生活”。我们作家不能只满足于深入别人的生活,更应该在这正起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中于非文学的领域内也以具有鲜明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去创造生活。我们常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点正在于他要创造性地掌握历史和在现实中体验历史。我很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考葛兰西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实践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积极改造周围世界的人。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丰富的想象力来自艺术的启示、生活和体验与记忆。但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属于别人的不论多么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领域中哪怕是进行微小的变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的话,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
至于我,我要和我区的同志们一起办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刊物——《文学家信息》。基于对我们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在现代都面临着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这种认识,基于我们现在的信息生产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被知识的海洋所淹没却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必需的知识这样的现状,这家刊物专为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从知识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家刊物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广泛摘编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民族和国际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如正在发展的空间科学、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况。它将成为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资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闻性,只注意努力扩大文学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知识面,要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文学的边缘上形成一门边缘科学,以促进和便利创作、研究、评论和阅读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自治区领导对办这个刊物的计划也感到兴趣。可是要把这个计划变为现实,肯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正因为有“想不到”,才能激发起活力,生活本身会不断地把它还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我们,如不愧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就要像我们在北戴河时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
谨颂伏安!
贤亮
1984.7.25.
无忧书城 > 边缘小品 >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