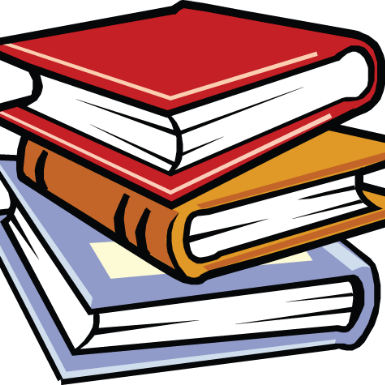和尹平认识,是在一九八○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一期学习班里。那时湛容、万隆等人虽然已经写过长篇,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著名;毕必成是我们的组长,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学员。时令正值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在热烈进行,知识分子都沉浸在解放感之中。在艺术上,我们似乎还处在一种“脱毛”阶段;我们的翅膀都还没有展开,都还没有对未来我们将经历些什么事有所准备。从窠里仰望天空,空间是已经够广阔了。以后,各自作了各自的探索,各自有了各自的甘苦,各自遇到过各自的幸与不幸,但毕竟各自都写出了各自的作品。
我们一别十一年。虽然有过书信来往,因为都忙着自己的事,也并不频繁。偶尔,在报刊上看到尹平的作品,如见故人,总是注意的。今天,他又出了一本集子。十一年中,他竟也“儿女成群”了。集中读了他给我寄来的几篇小说,首先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
如我这样的人,情节的大起大落,故事的曲折复杂,已经难以吸引我了。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倒是想在书中寻找小桥流水、豆棚瓜架的平静生活以抚慰自己,并且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在过另一种生活。尹平似乎正是在向这种淡雅的境界开掘。写英雄并不难,构思出离奇的故事也比较容易,难在从凡人小事中挖出悠远的或惊心动魄的题材。这就是契弗所以被人称道的原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干扰人类正常生活的,除开生态破坏、天灾地震等等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人为的因素,莫过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了。如天可怜见,我们中华民族再别搞自己整自己的政治运动,那么留给将来文学家去写的,大约也只剩下尹平现在所写的这类题材了。人类之幸运,也是文学之所幸。我以为文学就应该正常地反映人类的正常生活。战争和政治运动虽然创造出许许多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宁愿文学史上没有这些伟大的作品。“伤痕”也好,“反思”也好,又何必呢?“伤痕”不说已明,即使“反思”也不是好事情。如我这一代的作家虽然还在“反思”着,我想我们大概也是为了今后不再“反思”吧。
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
所以,尹平现在走的的确是一条较为宽广的文学道路。对于过去,他没有负担;对于现在,他没有偏见。并且,年龄又是他的资本。文学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不过,我并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出什么吹捧。现在和未来,文学上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成功者,除了应该具备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和特殊的感觉外,我以为还需有如池田大作所说的,“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无忧书城 > 边缘小品 > 别有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