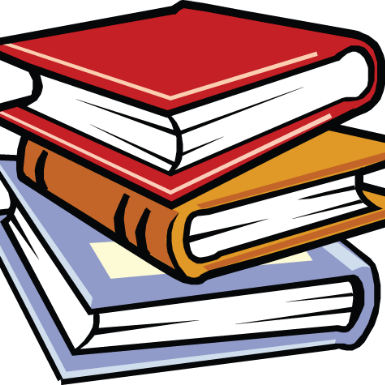大倌一掌击在龙卷风之上,那龙卷风自然动也不动,却猛地一阵摇摆。以大倌真气之强劲,也被它摆得头晕眼花。她心下暗道不好,果然那支无比硕大的龙卷风受激之下,发出一阵嘶哑的啸声,突然就是一沉。这一下猛地粗了一倍,带起的狂风携着势不可当之威,如海潮决堤,向着两人直扑而下。
大倌登时心中一滞,急忙运起掌力,急推而出。但这等天地之威何等猛烈?只听一声呜啸,大倌就觉一股腥味迎面扑来,身子宛如腾云驾雾般倒飞了出去。
耳中就听凌抱鹤急道:“你怎么样?”
大倌猛地清醒,一咬牙,道:“没事!让我来!”猛然就觉自己乃是被凌抱鹤抱在怀里,不由大羞,强挣着就要坐起,
凌抱鹤肃然道:“这等强攻不行,看我来对付它!”也不待大倌反对,他手臂一紧,抱着她蹿了出去。
只见凌抱鹤轻功运开,宛如一道轻烟,绕开风势凌厉之处,向一股龙卷风背后避了过去。那股庞大的龙卷风猛扑而至,与他们闪过的龙卷撞在一起,立时便是一阵暴响,去势稍缓。当下,凌抱鹤又向着下一支龙卷风奔去。这样不住躲避,背后的龙卷风越来越大,而小的龙卷越来越少。凌抱鹤、大倌二人乘云御气,后面紧跟着一条大大的灰色沙龙,当真凶险万分。
突地就听凌抱鹤道:“你相不相信命运?”
大倌摇头道:“我不相信。就算有命运,也要诞自我手中。”
凌抱鹤看着她,脸上慢慢漾起一丝笑容,淡淡道:“我和你不同,我相信的。现在我忽然有个奇怪的念头,也想说服你相信这点。”
他仰头望了望夭矫天空的灰龙,笑声中竟含了种奇异的秘魔之声:“所有的沙龙都聚在这里了……我突然有一个直觉,好像命中注定这沙龙并不能杀死我们,你相信么?”
他的双目中突然射出一阵疯狂的光芒,大倌看得心中一寒,只觉身子一顿,凌抱鹤竟然止步不走,就这样仰面对着那庞大到不可思议的龙卷风,竟似乎在迎接它的到来,让它将两人一起撕裂!
大倌心下一阵大急,忍不住出力挣扎。但她两臂被凌抱鹤紧紧抱住,穴道也隐隐受制,却哪里能挣扎得开?眼见那龙卷风越来越大,灰色渐转成墨色,终于轰然一声,将两人一齐吞没。
死亡已迫在眉睫,而大倌突然觉得,此刻和凌抱鹤一起,其实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
沙圈骤然扩开,然后突然收紧,这等剧烈运动所引发的巨力顿时压得铁恨跟二小姐喘不过气来。二小姐的娇靥憋得通红,只觉胸口一阵跳动,仿佛心脏都要从腔子里跳了出来。铁恨伸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皮套,大声道:“套在头上!”也不管二小姐反不反对,一扬手,给她套在了头上。那皮套甚大,连二小姐上半个身子都给盖住了。
当下,铁恨猛吸一口气,右拳轰然击下。漠上沙土久经吹磨,本就松软软地不甚结实,铁恨这一下全力出手,当真有崩山坏岳之能。就听“卡拉拉”一阵大响,沙地被他击出个一人深的大坑。铁恨更不怠慢,拉着二小姐就跃了进去。耳听噼里啪啦地一阵响,大风卷起的沙土层层落下,顿时就将他们两人盖了起来。
二小姐先前还一阵惊惶,但随即觉得那沙石压在身上并不特别难受,不算很重,手脚尚能微微转动。尤其惬意的是,铁恨套下的皮套中竟源源不断流出新鲜空气,虽被压入地下,却并不十分憋闷。那地面上的大气呼啸、龙卷肆虐,这一埋入沙中,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了。相较那冲突激荡,这地下可真是乐土了。
大倌就觉身子被用力摔了出去,高速的旋转登时让大脑中一片空白。她武功虽高,终究天威难抗,当此之境,也不再挣扎,紧紧抱住了凌抱鹤,就觉凌抱鹤也同样紧紧抱住她,身形微微颤抖着。
一时之间,大倌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
本来几乎已脱了风暴之灾,却被此人突发奇想,说了几句关乎命运的废话,就自个儿跳入了地狱之门。大倌忍不住想破口大骂,但身子感觉到凌抱鹤轻轻的颤抖,猜想他定然也是从未见过此等塞上荒漠的天地之威,此刻想必已经吓到极处了,何必再骂他呢?
大倌暗暗叹了口气,反而怕凌抱鹤一失手落入风暴中,转眼就被绞碎了,当下将他抱得更紧了一些。有心以掌力硬破龙卷风而下,但这龙卷实在太过巨大,一个不好,反而立即便有性命之忧。好在按照经验推算,这次暴风没有多久也就该结束了。只要挨过一时三刻,那便极有得救的希望。
当下不敢多耗体力,瀚海长风掌的内息缓缓吐出,将自己跟凌抱鹤护住,任由龙卷风将他们两俩卷得越来越高。越达高处,压力便越强大,初时仿佛周身都被绳子勒住,到了后来,这绳子收缩成铁箍,箍得两人浑身生痛。风压逼迫,几乎连口鼻都张不开了。
一时又升了几十丈,大倌便觉神智也快给压得散了,突然,似有似无之间,头顶的天空似乎裂开了一道很小的口子,露出一丝湛碧的天色来。这一喜当真非同小可。大倌急忙用力睁大了眼睛看时,那一道湛碧越扩越大,有如春神降临,风度玉门关一般,霎时席卷过整个天空。横绝天际的龙卷风仿佛毒蛇被一刀刺中了七寸,极力挣扎了几下,突然暴跌而下!
瀚海长风,起得快急,落得也快急。头上的一痕青天恰恰初露,一下便如绸布撕开个头一般,稀里哗啦,片刻已是晴空一片了。天气一晴,那庞大的龙卷风立时就如雪狮向火,黯然消解下去。轰然暴响中,疾旋陡然停止,就如万丈高楼坍塌一般,垂直倒了下去!那被龙卷风卷起的沙土,何止千担万担?这一落下,就如天坤倒挂,黄茫茫的沙土布成一条几十丈的天路,层层堆叠,刹那间在大漠上堆起了一个百余丈的高台。
且喜凌抱鹤与大倌被风势吸得老高,此时埋得便不是很深。大倌掌力连运,击开一个大洞,顺手将凌抱鹤也拉了出来。
但见晴空一碧无翳,玉滑如洗。长风吹了多时,此时的天幕就如最通透的琉璃,再也看不到丝毫瑕疵。当中一轮清幽的明月,孤独地高悬着,彩光滟滟,将大地照得一片通明,却见不到一颗星。
这天地间仿佛只有这轮明月,此外再无一物。风声既息,寥廓天地间便再没有别的声音,越发显得这座天造地设的高台孤独而苍茫,人在其上,就如木石化就的一般。
大倌走到台边,向下看了看,那沙台极高,灰茫茫的几乎看不到地面。壁立千仞,更如悬崖峭壁一般。
大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狂笑:“没眼的老天!你有本事,怎么不杀了我?是你没有这能耐,还是你不敢!枉有人打着你的旗号,说什么行侠仗义,你却好像缩头乌龟,脑袋都不敢露!你算什么老天!快快滚出来,再吃我一剑!”
大倌摇了摇头,知道凌抱鹤的疯病又犯了。
此人不知如何,行事总有些颠倒错乱,当其好时,那便是风流蕴藉的浊世佳公子,说出话来让人说不出的欢喜;当其不好时,则变得狂猛凶狠、浑身邪气,令人心冷。
大倌不由自主想起他在比武高台上所说的话:“眉疏不画,自青于黛,颊淡未扫,更赤于脂。外物不御,心正眸中,当真是天上之人。”他那时的目光清澈有神,自己莫名地便觉他说的一定是真话,竟相信了他。哪知后来他突然转变,难道竟是戏弄自己的么?但观他疯疯癫癫,似乎先前那个面色温柔的凌抱鹤并不是他。究竟孰是孰非,大倌可越想越糊涂了。
眼下高台百丈,只有一轮明月与此狂人相伴,明月是高悬着不理人,凌抱鹤也是怒骂着不理人,大倌怔怔地看着他,想着自己的心事,不由得痴了。那轮明月的万点银辉撒下,照得她是孤零零的,凌抱鹤也是孤零零的。
大倌素以男儿自居,这等儿女情怀,可说是从未曾领略过的。她在铁木堡中久称堡主,威严素著,哪有人敢对她说这些风言风语?何况她武功绝伦,铁木堡又僻处塞外,见的人本就少,就算见了,也当她是一代女侠,谁敢失了半点礼数?是以她虽长到二十五岁,轻薄欢爱的话,却是第一次从凌抱鹤口中听到。哪知竟是这轻轻的几句话,加上一阵暴风,就此便打开了少女尘封的芳心。自然,凌抱鹤并不知道,大倌虽然有所颖悟,却也并不很清楚。
苍苍茫茫的夜色中,凌抱鹤突然仰面摔倒,怒骂声立绝。他躺在地上,看着这轮冷碧的明月,竟似已看得痴了。一时两人一个想着心事,一个望着明月,都是静静地一动不动。大漠之上,一片寂静。
良久,凌抱鹤突然轻轻道:“今晚的月亮好圆啊……”声音温柔无比。
大倌心中一动,难道他竟是对自己说么?凌抱鹤一语说完,更不再说,依旧盯住那轮明月。大倌心思潮涌,突然就见凌抱鹤坐起身来,喃喃道:“三年大比之日就要来临,我读了一辈子的书,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不辜负家亲的期望,可是家中贫穷,无处筹借路款,这便怎生是好?”
大倌听他说得奇怪,心下狐疑。大比之日?难道武林中有什么别的比武大会,每三年就要召开一次么?怎么自己却从没听说过?凌抱鹤年轻豪侠,怎么会说什么家中贫穷,无处筹借路款?一时百思不解。
偶然与凌抱鹤相对,但见他两只眸子全陷于深湛的紫色,映着清冷的月光,幽幽深紫,妖异至极。大倌心中一沉,知道有些不好,但究竟不好在哪里,却也说不出来。
凌抱鹤也不理她,慢慢在沙丘上踱着步,自己喃喃道:“这便怎生是好?这便怎生是好?”
大倌听他转来转去,口中所说的尽是什么大比、参试、期望云云,越听越是糊涂。凌抱鹤目中的紫光越来越盛,所说的话也越来越模糊。
突然,他抬头对着大倌道:“你肯帮我么?”
大倌见他满面焦急地望着她,眼中尽是求肯之色,虽不明白他言下所指,却也不愿让他失望,当下柔声道:“你只管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无不尽力。”
凌抱鹤嘴唇动了动,仿佛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脸上的痛苦之色却越来越盛。
大倌急道:“什么大比?你是要钱?还是要我陪你去?你说吧,这世间的事情,还当真有我俩做不到的么?”
凌抱鹤突然打断她道:“我没有钱!”
大倌吃了一惊,只听他一字一字继续道,“我要把你卖给南村的洪大爷,他们一会儿就带人来,你收拾收拾跟他们走吧!”他闭着眼睛,仿佛在聆听什么,又道:“你不要怪我无情,我为了上京赶考,只能出此下策啊!你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你好好跟着洪大爷过日子,他说了不会亏待你的。”
大倌听得一片茫然,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只听凌抱鹤继续道:“宝儿也跟着你去吧,我此去京师,也无法带着他……等我有一天飞黄腾达,自然会接他回去的。”
他这般说故事似的自说自话,眼睛闭着,在清冷的月光之下,当真如鬼魂附身一般。大倌极少与别人倾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静静地听他说话,凌抱鹤要说到什么时候,她便听到什么时候。
突地凌抱鹤双目睁开,直盯在大倌脸上。他仿佛这才发现大倌这个人,又仿佛大倌是他十世的仇人,目光中尽是阴狠仇辣之色。
大倌给他看得周身不自在,强笑道:“你……你怎么了?”
凌抱鹤一字一顿,咬着牙道:“我要强暴你!”大倌又怔住了。她虽已知凌抱鹤行事大异常人,但却没想到他异常到这般地步。
瞬息之间,凌抱鹤飞身而起,一把就抱住了大倌,死死握住她双肩,往沙地上压下。大倌大骇之下,一时忘了抵抗,凌抱鹤手指用力,“哧”的一声轻响,将她上衣撕开了一道口子。
大倌倏然抬手,右掌已然卡在凌抱鹤的脖子上,将他整个人提在半空中,怒道:“你疯了?”她一边左右开弓,“啪啪”打了凌抱鹤几个耳光,一边怒道,“原来你是个畜生!”她此时心中怒气勃发,并未刻意约束真力,这几个耳光打下来,凌抱鹤双颊登时高高肿起。
突然,大倌猛地出拳,轰然击在凌抱鹤胸前,怒道:“太让我失望了!”她一面怒喝,一面出拳,立时将凌抱鹤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凌抱鹤此刻却如突然怔住了一般,口大大张开,似乎想说什么,却一点都说不出来。大倌盛怒之下,也不去管他,一拳拳猛击而下。凌抱鹤被她真气冲撞,就如风筝一般,在长风中飘摇。
渐渐大倌的怒气稍稍发泄,卡住凌抱鹤脖子的手稍微放松,将他的脸降下,先打了四个耳光,再喝道:“你现在还想不想强暴我?若是你还能站起来,我不妨成全你!”凌抱鹤闭目不答,如同死了一般。
大倌冷笑道:“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下辈子投胎再来吧!”手臂运劲,就待将他抛出。
突然,凌抱鹤嘴唇抽动,仿佛说了什么。大倌凝神静听,凌抱鹤这两天被她一次次重伤,虽然有不死神功护体,却也已虚弱得很,其声极为细微,怎么也听不清楚。
大倌心中一动,俯身在他嘴边,大声道:“你有什么遗言,只管告诉我,我必为你办理……”凌抱鹤紧紧抱着她,似乎想从她身上感到一丝温度。他的身体剧烈颤抖,心跳的声音极度虚弱、又极度沉重。大倌眼中神光跃动,再不能推开他。
凌抱鹤嘴中吐出一串血沫,轻轻念道:“对……不……起……娘……对不起——”
大倌猛然就觉胸口一凉,她慢慢低头看时,就见清鹤剑直没至柄,已然完全插入她身体中去。大倌忍不住身体一个哆嗦,再也抱不住凌抱鹤,身子踉跄后退,终于“砰”的一声,坐倒在地上。她的眼中闪过一阵或是伤痛、或是爱怜的神光,盯在这柄秋水一般的名剑上。银色的剑柄在朗朗明月映射下,闪着难以捉摸的光芒,既明亮又阴冷,既灿烂又无情。
大倌勉强想挤出一丝笑容,却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
月色如水。
良久,凌抱鹤僵硬的身子突然动了动,他茫然地爬了起来,眼睛无神地环顾着这苍茫的大地。他的目光终于停留在大倌的身体上。方才一剑虽然凌厉,但大倌的真气强悍至极,终于守住了最后的一处心关,让她停留在弥留的岸边。凌抱鹤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从肺腑发出一声凄厉地叫喊,在夜空中远远地传了出去。
无忧书城 > 武林客栈·日曜卷 > 第7章 天意高隔缈难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