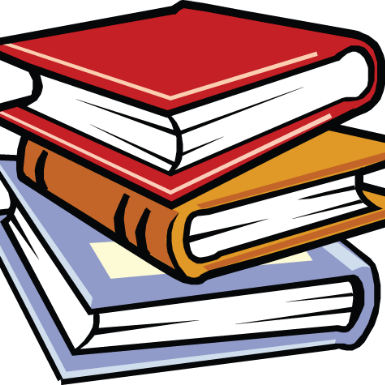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找到徐副使了——!”
天明时分,锦衣卫们在御花园的一片假山后,发现了悄然漫出的一大滩血。
云起胸前插着拓跋锋的绣春刀,刀刃微妙地穿过内脏间隙,从背后透出,将他钉在假山上,卡在肋骨中的长刀支撑住了他的体重。
荣庆吸了口气,吼道:“快!传御医!”
云起失血过多,脸色变得苍白,躺在病榻上更发了足足数天烧。
御医会诊后判断出其性命无碍,但血液流失剧烈,又大量消耗一番体力。
朱元璋翻开御医们的诊断书。朱棣笼着袖子,静静站在殿中,不时打量荣庆神情。
朱棣开口道:“儿臣的不是,只想着那突厥狗父母双亡,方将其送进宫中当差,不料这野……此人竟是与北元有勾结,险些害了允炆。”
朱元璋沉思不语,许久后道:“荣庆,你且退出去。”
荣庆走后,朱棣低声道:“父皇,云起与允炆一同长大,若……只怕寒了这一应锦衣卫的心,连带着允炆,还有徐雯。”
“雯儿与云起同母,俱是庶出……父皇,今年死的人够多了,给徐家留点香火罢。”
朱元璋放下奏折,点了点头。
正使拓跋锋犯下重罪脱逃,副使徐云起伤重,张勤为国捐躯。
嚣张跋扈的锦衣卫在这一年里,竟是损失了两名成员,恶犬们终于要夹起尾巴做人了,荣庆底气不足,挑不起担,更无云起这般显赫出身。
拓跋锋之罪未定,谁也说不准朱元璋哪天心情不好,便要将这四十八名锦衣卫尽数拖去砍头。锦衣卫的前途,此刻尽数寄托在云起身上。
云起伤未痊愈,只倚在庭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昏昏沉沉,晒着太阳。
秋天一到,便要准备过冬了。
“云哥儿。”一名侍卫笑道:“你打不起精神,弟兄们也都病恹恹的,高兴点儿罢。与你回房下棋?”
云起揉了揉太阳穴,道:“下棋伤脑子,我晒会儿太阳便进去。”
午后阳光暖融融地铺在身上,那侍卫又道:“徐家不是有铁券么?你爹是功臣,老跋那事儿应不到咱身上,别胡思乱想了。”
云起笑道:“那玩意儿在我二哥家呢,皇上要真想治我的罪,你还快马加鞭去扬州,讨了免死金牌来用不成?”
那侍卫笑了起来,忽听院外人声道:“孙韬!当朝铁券也敢开玩笑,我不过走了一年,这大院里便无法无天了?!”
孙韬立马大骇,喊道:“蒋师来了!”
蒋瓛卸任年余,再回到锦衣卫住处竟是头一遭,霎时间房门大敞,侍卫们匆匆奔出,挨个立于院中。
云起忙起身道:“师父怎么来了?”说毕瞥向跟在蒋瓛身后那人,竟是朱棣。
蒋瓛一路穿过大院,云起正要把来客让进厅内,蒋瓛却道:“搬两把竹椅来,便在此处坐了。”
说话间便有侍卫去搬椅泡茶,蒋瓛又朝一人吼道:“李渔!何事衣冠不整!你的帽子呢!”
那被点到名之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声告罪,回房寻侍卫冠。
少顷云起领着众侍卫立于院中,庭廊前两把竹椅间摆了个茶几,燕王朱棣先坐了,蒋瓛这才入座,扫了这数十名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一眼,嘲道:
“拓跋锋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初我是如何交代你们的!”
云起躬身道:“师父教训得是,您卸职一年,众弟兄确实松懈了。”
蒋瓛峻声道:“孙韬出列,我卸任前怎么对拓跋锋,对你们说的?”
孙韬惴惴上前一步,答道:“蒋师吩咐:做人如用兵,须谨记孙子兵法之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蒋瓛冷笑道:“瞧瞧你们现下的模样,不动如山?谁做到了?!拓跋锋平时怎么约束你们的!”
众锦衣卫齐齐一凛,挺直了背脊。
蒋瓛又嘲道:“成日称兄道弟,嬉皮笑脸,简直就是一群土匪!贼寇!乌合之众!拿着尚方宝剑当棉拍,这就是锦衣卫的模样?!”
“二十四卫!锦衣为首!现瞧瞧你们自己,瞧瞧……”蒋瓛把茶盏重重一放,欺近前来,揪着一人衣领,将他拖出列,怒道:“除了当个衣裳架子,小白脸,操廷杖打那手无缚鸡之力书生,还有半分男人的模样么?!娘——们!”
说毕竟是气极,一脚将那倒霉鬼踹倒在地。
蒋瓛辈分极高,发起火来,院内噤若寒蝉,唯一敢插嘴的,便只有座上王爷。
朱棣见老头子满脸通红,只恐怕其训徒弟训到一半要脑溢血倒地,闹大了麻烦,忙劝道:“蒋老莫动怒,如今不比……从前了,伤了身子不好,不好。”
朱棣一面嘿嘿笑,将蒋瓛请回座上,蒋瓛瓮声道:“今日来本不是为了训你们,实是心中有气,不吐不快,现说正事,徐云起,出列。”
云起上前一步,凛然道:“徒儿在。”
蒋瓛捋须打量云起片刻,而后道:“你与拓跋锋同门多少年了。”
云起暗自心惊,答道:“四岁入宫,到如今是十三年了。”
蒋瓛道:“十三年,你如何对待师兄?!”
云起颤声道:“那夜师兄下毒……暗害皇孙……”
蒋瓛怒道:“你与他生死相博,拔刀相向,是还不是!”
云起道:“是!但当时情形,师兄犯了大罪,若放他走,云起便是不忠……”
蒋瓛道:“然而抽出腰间绣春刀,对自己的师兄下手,便是不义!”
云起吸了口气,答道:“师父,忠义不能两全。”
蒋瓛道:“很好,今日打你,便是为了这忠义不能两全!取铁杖来!”
众侍卫骇得手脚冰冷,蒋瓛威势极盛,又道:“都不听了?可是要我去取?!”
数名侍卫忙转身入厅,取来两根粗若儿臂的铁棍,蒋瓛素来管教手下极严,锦衣卫少年入宫受训时,无一不挨过这铁棍痛打,每次俱是皮开肉绽。
然而云起自小到大,却是头一次尝到这铁杖的滋味。
“从前都是拓跋锋替你挨杖,如今,也轮到徐副使你亲自生受一回了。”蒋瓛冷冷道:“架住,八十杖,打!”
众侍卫犹如遭了晴天霹雳,云起却是自觉伏下,把眼睛一闭,道:“打罢。别来虚的。”
那持棍的两名侍卫无计,只得咬牙抡起铁杖,打了下去。
云起痛哼一声,杖落发出闷响,蒋瓛又道:“你们平素在朝廷上玩的猫腻,别以为我不知道,且轻着点打,打完再来八十杖。”
那掌杖锦衣卫心中打了个突,不敢再放水,只得使劲真打,唯恐蒋瓛不满意。
杖劲一重,云起登时痛喊。
蒋瓛在那杖声中悠然道:“忠义不能两全,保住了拓跋锋,你就是杀头诛九族的大罪!”
云起咬牙苦忍,断断续续道:“师父……教训得是。”
蒋瓛道:“拓跋锋捅你一刀,成全你忠名;现打你便是让你谨记,当初拓跋锋替你挨了无数棍,如今让你一并还了!”
朱棣看在眼中,嘴角微微抽搐,显是头一次看到此惨无人道的刑罚。
大凡治军法,顶多是二十杖,四十杖那般打,且又是木棍。
廷杖乃是铜铸,也不过四十杖,再打下去,只怕便要当廷把人活生生打死,何曾听说过要挨足八十杖的规矩?!
朱棣咳了一声,忍不住道:“那个,蒋老。云起他……是不是有点……”
云起已被打得昏了过去。
蒋瓛冷冷道:“求一句情,再加十杖。”
朱棣闭嘴了。
待得尽数打完,云起腿上到处是血,再找不到一处完好的肉,就连飞鱼服也被打得破破烂烂。
蒋瓛又道:“两人扯手,两人扯腿,摔!”
朱棣霎时魂儿被吓飞了七成,发着抖道:“不能摔!蒋老!再摔就死了!”
蒋瓛捋须道:“燕王要求情?摔两下。”
“……”
四名锦衣卫抬着云起,将其举起,又重重摔在血泊中。
云起已无意识,肺部被激,哇地吐出大口鲜血,和着一枚染了血,洁白的臼齿,竟是在苦忍时把牙给咬碎。
朱棣惊悸地看着云起,不住喘息。
蒋瓛终于达到了目的,缓缓道:“来四个人,将他身上血抹了,取担架来!抬着到太和殿去,老夫要面、圣。”
朱棣吁出一口气,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太和殿外。
朱棣守在殿前,侧耳听着殿中对答。
朱元璋对蒋瓛仍是极其器重,二人谈了许久,又听蒋瓛低声道出“北元”“突厥”“探子”等字眼,朱棣心头方放下一块大石。
少顷后,只听朱元璋道:“朕知道了。”
蒋瓛方退了出来,锦衣卫入内,抬了担架上的云起,回到大院中。
朱棣伸手去探云起鼻息,呼吸微弱。
蒋瓛缓缓道:“不妨,性命无碍,取他颈下那布包来。”
朱棣解了云起贴身布包,蒋瓛又道:“内有一枚枯荣造化丸,喂他服下,一日便好。”
朱棣打开那布包,蹙眉道:“蒋老,你方才说……什么丸?”
蒋瓛愣住了,朱棣托着那布包让看,内里只有一张泛黄的符纸,与一枚碧绿色的麒麟型玉佩。
“……”
这下轮到蒋瓛遭了晴天霹雳。
只听蒋瓛颤声道:“张……道长赐的那枚……灵丹。怎没有?云儿给谁吃了?”
朱棣五雷轰顶,与蒋瓛相视良久,道:“你……蒋老,这玩笑开不得,他可是我小舅子!要有个三长两短,贱内会……”
蒋瓛张着嘴,想起朱棣家“贱内”的厉害,霎时定了三秒,而后吼道:“太医!传太医!不好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云起小身板儿刚躲过飓风又遭了冰雹,失血过多,挨铁杖猛打,导致椎间盘脱出,外加精神饱受命运的来回□□——居然没死,也真是个奇迹。
朱棣顾不得求神拜佛,先熬了一大碗浓浓的千年老参汤,扳着云起的牙关灌下。
继而联合六名御医会诊,同时派出亲卫快马加鞭,连夜出京,前往北平。
亲卫跑死了三匹马,带回来一个锦盒,盒中装了一只朱眼冰蟾,以及“贱内”的一封信:
我的心肝!
你上辈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
朱棣!!!!!!
云儿若是有个好歹!
我徐家全家纵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朱棣背脊发麻,朝那亲兵道:“夫人……目前情绪还稳定吗?”
亲兵答道:“夫人请来全北平的道士和尚,一半念经,一半开坛做法。点了满府长明灯,命全城百姓斋戒……说若是得不到小舅爷平安的消息……就……就……”
朱棣道:“知道了。”
那亲兵与朱棣脑门上俱是三条黑线。朱棣眼珠子转了转,仍忍不住道:“就如何?”
亲兵压低了声音,道:“就砍死……那个……弑君。”
朱棣点了点头,知道徐雯说的定是“砍死你全家”,这全家自然也包括朱元璋。
房内传来荣庆之声:“王爷,该换药了。”
朱棣取来冰蟾,以烧酒调了,灌入云起嘴内。烧酒极烈,一入喉云起便猛咳起来,朱棣忙端碗接了,喝进嘴里,继而抱着云起,缓缓喂了过去。
云起喝下灵药,低吟了一声,倚在朱棣怀中,沉沉入睡。
朱棣望着那跳跃不定的油灯火苗出神,不知在想何事,末了又看了看云起。
朱棣漫不经心道:“你与清儿……都是徐将军的眉毛,温月华的眼……你们的娘该得有多美?竟是生得出这水灵造化的姐弟来。”
云起微微挣扎,朱棣放开了他,让他平躺,拉过被子仔细盖好,端详云起片刻,而后痞笑着点了点头。
数日后,在朱棣黄金猛砸下,云起的伤势终于开始逐渐好转。
朱棣从年轻起便随军生活,习惯了亲力亲为,一介王爷,照顾起病人倒也不嫌苦累,每天为云起换药,缠绷带,喂药,俱是得心应手。
如此困了便伏在云起榻旁歇息片刻,饿了与锦衣卫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不知不觉已过了近半月。
云起睁开了眼。
那时朱棣正与几名锦衣卫在院内踢毽子,一听云起醒转,赶紧连滚带爬地冲进房内。
“内弟,你好了不曾?”朱棣紧张地看着云起涣散双眼,又伸出五指,试探地在他面前挥了挥。
朱棣比了个拳头,道:“这是几?”
云起道:“都给我出去。”
房中站满侍卫,忙一窝蜂地散了。
朱棣作了个投降的手势,悻悻转身出门。
云起虚弱的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怒火,冷冷道:“王爷,你好大的胆子”
朱棣唏嘘道:“还好你咬碎那枚不是门牙,否则说话漏风……”
“纸钱是你交给他的?”
朱棣收起玩笑的表情,云起缓缓转过头,与其对视。
朱棣目中杀机一闪即逝,云起道:“墙边有刀,杀了我就是。”
朱棣一笑置之,答道:“莫开玩笑了,咱是一家人,杀谁也不能杀你。”
朱棣一抖袍襟,于那榻沿上坐了,左脚架在右膝上,拍了拍黑靴,随口道:“这顿打,说到底是姐夫害的,现记在心上,来日补你。”
云起目中尽是厌恶之情,道:“滚远点!”
朱棣丝毫不生气,反而笑了起来,饶有趣味地打量云起,眯着眼道:“小舅子,你生气的模样,与你姐像得很,有人说过么?”
云起不答,冷冷道:“你把拓跋锋当作什么了?”
朱棣悠然道:“自然是儿子,不然能把他当什么?”随即又望向云起,调笑道:“姐夫从小可没什么青梅竹马来着,也没那玉佩拉绣花扇拉的定情信物……”
云起失控般地大吼道:“你没把他当人。没人把他当过人!”
朱棣收了笑容,认真道:“云起,眼见为实,你未曾亲眼所见,从我收养拓跋锋那时起,塞外凡是突厥一族,便都托着他的福,方保住了性命。”
“狼部本不是姐夫杀的,元人逃窜那时自己下的狠手,姐夫救了他性命,又将他送进宫来,每年给他族人送牛送羊,府上凡是有姓拓跋的突厥人来托庇……”
云起嘲道:“若是你有朝一日当了皇帝,就送他回克鲁伦河去?许给他多少封地,多少兵,多少女人?多少牛羊多少财物?”
云起说到激动时又不住急促喘息,朱棣忙上前抱他坐起,却被云起咳嗽着推开。
朱棣倒也不恼,笑道:“没有许他,倒也终究是他该得的,我厚葬了他部落中人,又救了他全族性命,把他养到五岁,将其身份坦言告知。”
“没有丝毫隐瞒。又教他突厥语,让他牢记自己是何人。换了是你……你会为我卖命不?”
朱棣微笑道:“小舅子,拓跋锋那性子你不懂?突厥人脑子倔得很,你对他好,他便死心塌地报答你,记了仇,亦会一心一意来报仇……狼崽子不就是这脾气?”
云起反讥道:“死心塌地报你收养之恩,最后等到了一杯毒酒。”
朱棣色变道:“什么毒酒?”
云起蹙眉与朱棣对视。
朱棣表情如坠万丈深渊:“他喝了毒酒?!”
云起疑道:“那鹤顶红不是你送的?”
朱棣半晌说不出话来,而后方道:“死了?!”
云起茫然无比,脑中混乱一片,朱棣猛然抓着云起的手说:“你……小舅子,你不是已经放走了他?!那夜事发,二更时我派人去牢中救他,回报狱卒死了,这案才发,你……”
云起挣道:“没死!”
云起看了朱棣一会,缓缓道:“那夜有人送了毒酒,要杀他灭口,这可奇怪了,会是谁?难道是皇上……?”
朱棣道:“中的何毒?你将他送去何处?”
云起摇了摇头,道:“我给他吃了枯荣造化丸,那药能解百毒……接着送他上船,到扬州去了。”
朱棣如释重负道:“回头我让他给你写封信,你便知端倪。”
云起抿唇想了片刻,头又开始疼了起来。
朱棣转身去取笔墨,一面絮絮道:“你养伤罢,既是好了,写个条子给你姐,否则这辈子,我就别想进家门了。”
云起一肚子气消了七成,劈手接过笔,随手写了句“朱棣王八蛋”,接着拍了回去。
王八蛋诚恳道:“内弟,这话等于骂当朝皇上是王八……”
云起怒了,把“蛋”字涂掉,王八方笑嘻嘻把那纸条折好塞进怀中,道:“这就走了,勿念。”
朱棣转身那瞬间,云起冷冷道:“我娘是舞烟楼红牌,皇上取应天府时,兵荒马乱,认识了我爹。”
朱棣听到这句,忍不住转身,云起又道:“我姐弟俩是庶出,娘的出身又不好,我就是个当一辈子狗的命,跟皇孙再铁,也是白搭。”
“朝中言官不会让我封官荫子的,你省点儿罢,有这心思不如去讨好六部的人。”
朱棣挠了挠头道:“姐夫连自个娘叫啥还不知道,当年老头子与陈友谅顾着打到西,又打到东……连我娘都给弄丢了。现认了马皇后当娘,仔细说起来……”
朱棣恢复了那兵痞子的一贯笑容,得意洋洋道:“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说毕又挖苦道:“内弟,你早在第一次喂药时就醒了,装昏装了十余天,敢情懒得动,等王爷伺候呢。”
朱棣转身离去,当天下午便率领亲卫离开了南京。
云起躺在床上,闭着眼,轻声道:“没什么好难过的……师兄,保重。”
“哭啥,都几岁了,大男人哭哭啼啼……”
小拓跋锋蹲在床边,打量小云起,蹙眉不悦道:“别哭了。”
小云起抽泣道:“我家里死了人……”继而一吸溜鼻涕。
小拓跋锋答道:“哦。”
两人定定互相凝视片刻,小拓跋锋又道:“我家里人也死光了。”
小云起又哇哇大哭起来,道:“死的是我爹!我每个月的两钱银子没了!”
小拓跋锋又道:“哦,没了。”
“脑袋怎么破皮,过来,师哥给你揉揉。”
小云起一把鼻涕一把泪道:“磕头磕的……”
小拓跋锋同情地摸了摸小云起的头。
“叫爹。”
“……”
小云起斜眼去乜小拓跋锋,那眼神,像只不太信任人的脏兮兮的小猫。
小拓跋锋漠然道:“叫声爹,以后师哥当了锦衣卫,俸钱都给你,一个月二两银子呢。”
小云起一声“爹”到了嘴边,终究叫不出口,恹恹道:“还是不要了,爹不能乱叫。”
小拓跋锋看他那架势,像在酝酿情绪,只怕不多时又要开哭,忙让步道:“不叫也给你好了。别哭。”
“不……我要哭。”
“不要也得要。”
“给你两钱银子,让我哭一会……”
“不许哭。”
“哇啊——!师哥,我爹死了……我爹死了!!”
自那天起,小拓跋锋每个月便能拿出两钱银子给小云起。
天知道十二岁小孩哪来的钱……
然而那不重要,十岁至十五岁,每月两钱银子,共十二两;十五岁至十九岁,每月二两银子——普通锦衣卫俸禄,共九十六两。
十九岁至二十岁,每月三两银子——锦衣正使官俸,共三十六两。
拓跋锋当差这许多年的所得,尽数给了自己,一分钱也没乱花,果然说到做到。
云起把账本烧了,银钱数默默记在心里。
——卷一·麟之为灵·终——
※※※※※※※※※※※※※※※※※※※※
我~~T_T
我是数学白痴~~
算钱一点也不好玩啊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