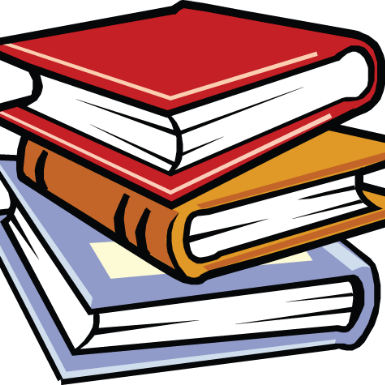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石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
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我知道,我一刹那间的感觉之中,压缩了人类亘石以来的经验。
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芦苇在路边沙沙作响。路边的排水沟里潺潺地流淌着清水,一碧到底,如山泉,如小溪。两三寸长的小鲫鱼一群群地聚在沟边绿茸茸的水草底下,时不时露出它们黑色的小脊背,或如点点光斑那样闪现出它们银色的小肚皮。四处是黄色的阳光,空间既广裹又沉寂。温顺的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象两条凹下去的铁轨。我在路当中走着,脚步既滞重又轻盈。一会儿,脚下的浮土缓缓地腾空而起,象清晨的雾气,使一切都变得迷蒙而柔软。我仍然沿着车辙朝前走。感觉到我有奇异的视力,能透过浓密的黄尘看到我意识下面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了一只猫:灰色的,夹着白色的条纹。它弓着背警惕地站在前面,前腿和后腿分别跨在车辙两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好象随时都想逃跑。
那是“我们”丢失的猫,我知道。
忽然,猫不见了,象影子一般消失了。
梦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我又看见了排水沟里游着四只鸭子。从它们的脖颈和撅起的尾巴上,我能断定其中有两只母鸭。它们和猫一样,也是灰色的,翅膀中杂着白色的羽毛。它们静悄悄地游着,沿排水沟溯流而上,似乎有意要把我引到感觉记忆的深处。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它们后面。但它们在一片芦苇茂密的水洼中,摆了摆屁股,兜了一个回子,却顺着洄流钻入了草丛。
我仍然在如雾似的黄尘中向前走。我吃力地拔着滞重的两腿,却又走得非常轻盈,如一只顶着风飞翔的鸟儿。
走过了水洼,鸭子又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了。但那不是四只大鸭,而是四只小鸭。通体金色的绒毛,在黄色的尘雾中它们好似会渐渐地溶化,会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之中。然而,它们确实在欢快地游着,一面游还一面歪着小脑袋傻乎乎地看着我。那向上弯曲的嘴角好象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我忽然意识到,刚刚见到的四只大鸭就是“我们”原来丢失掉的鸭子。这四只小鸭正是它们雏期的模样。
时间在向回倒流。那么我会不会恢复到那个时期,即使是在梦中?
于是,我在时间中振竹向回游去,想去追寻那失去的影子……
可是,我的梦每次都到此中断,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憾的感觉,是一种梦中之梦。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那一片混沦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
太阳重又升了起来,蛾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否还活着。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梦用笔来补充、续接出来?真实地、坦率地、有条理地、清晰地记录下那失去的过去?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怎么能用观念中的道德来判断和评价生命的感觉?至于理智,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蛾子死去了,谁也不会为它生命如此短促负责,那么,谁又有权利指责它飞旋的弧度和途径?”
阳光直射着我,光芒好似穿进了我的肺腑,又好象是我在金色的光中浮起,离开了这喧闹的尘世。我趁我获得了这种心境,一种坦然的出世的心境,赶紧一跃而起,奋笔疾书。我知道,如果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又会改变我这个主意。
无忧书城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唯物论启示录》之一 >